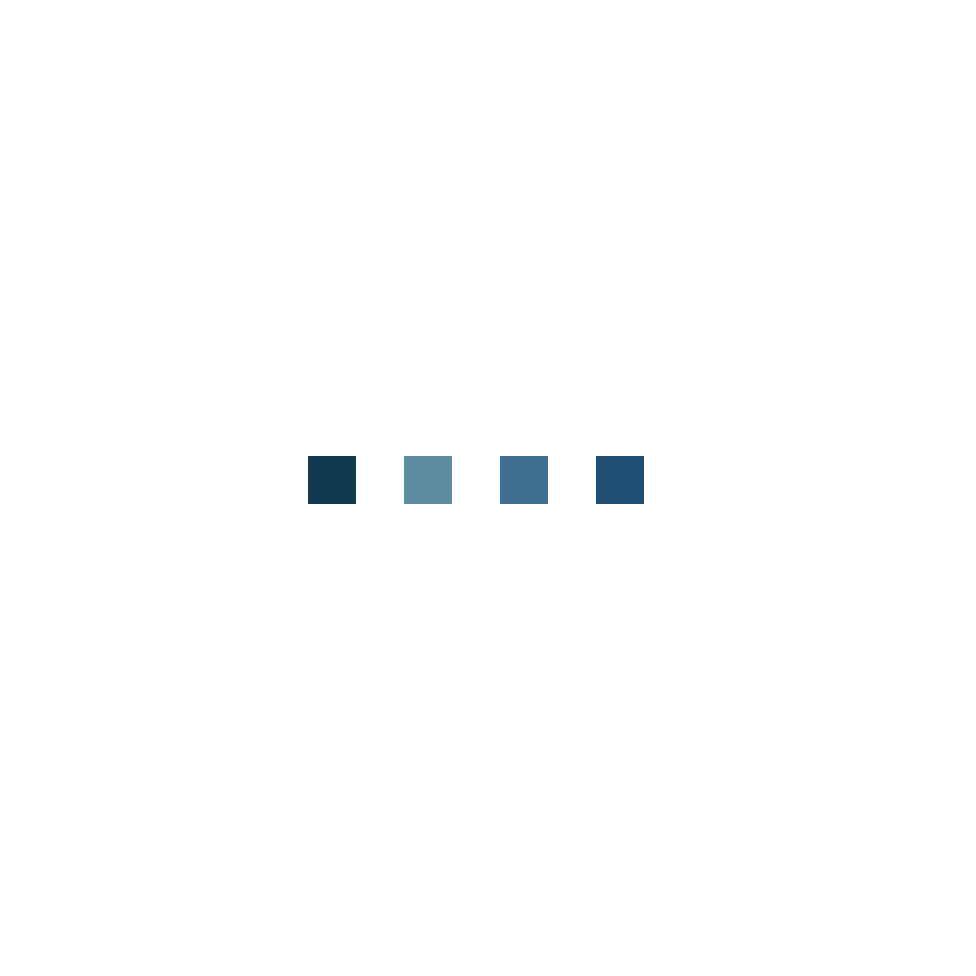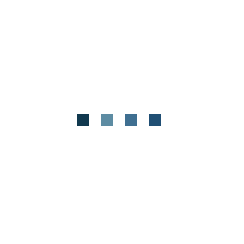鏡:其中一句你很喜歡的名言,是愛因斯坦說的:「唯一干擾到我學習過程的,是學校教育。」為什麼這句話特別打動你?可以與我們分享你的求學歷程嗎?
彼:我換過很多間中學,沒有一間能讀完,我年輕時已經…對所有事物都不感興趣。我7歲時去上學,試著要融入一切,卻永遠感覺像外人。國小畢業後我到了一間排名很後面的中學,每次去上學都感到更深的焦慮,學校對我而言簡直無聊,我在學校被霸凌、討厭去上學,所以我會在整面考卷上畫畫也不作答,他們就給我最低的分數,但下一次,只要我認真作答,就能夠打平分數不被留級。
為了逃過霸凌,我的生存法則就是跟看起來比較酷的孩子混,這樣別人就不敢惹我。我17、18歲時甚至因此在脖子上刺青,你就能瞭解霸凌是多麼沉重的事。可是我當時懂什麼呢?我還只是個情緒不成熟的年輕人,那個時期要我融入任何團體都很困難,我也不清楚自己能做什麼,只能專注在電玩世界裡,電玩真的給了我很多刺激。
我始終是個在外遊蕩的局外人,一直不太有辦法融入社會、跟人們和睦相處。所以我知道自己想要的不是那種八點到公司、五點下班的生活。我這種性格也反映在求學時的情況,我可以3天內讀完學校8週課程的教科書,很容易就能消化新資訊,但是可能很難100%了解或專注。處理跨領域的資訊對我來說相對容易,這也是為什麼我很喜歡辯論,我已經指導荷蘭政治人物的辯論技巧超過7年了。辯論就是讓自己像一塊海綿,彈性地吸收所有資訊,重點是用創意連結它們、產生獨特的見解,這樣才能用一個有邏輯的框架陳述論點,跟我在畫畫的過程也有點像。
鏡:當時你的父母如何陪你度過在學校的難關?
彼:我15歲時在學校表現不佳,因為我真的很提不起勁,之後我們才知道其實是我覺得一切都太無聊了。當時父母帶我去作性向測驗,考試結果說我可能會往廚師或是藝術家發展。當我爸爸問測驗顧問:「當藝術家能夠養家嗎?」對方說:「我的工作不能回答這個,我只能告訴你測驗結果,你們自己得決定。」
我媽媽一直非常支持我,她總能在我身上看到不同潛能;我爸爸則不太知道如何面對我,因為他不瞭解我的情況。他是一個自制力強、非常認真工作的男人,跟我處在非常懸殊的兩端。青春期階段的我,還沒找到自我認同,只能依附在父母對我的期待,所以我感覺好像不被允許做我想做的事,雖然我當時也並不清楚想做什麼,我開始退步,逐漸失去對未來的希望,只能著眼在每天生活的掙扎上。
後來我爸覺得我應該去讀商業相關的科系,因為當個藝術家要養活自己不容易,所以我當時否定了當藝術家這條路,可是當我21歲嚴重憂鬱到入院治療時,精神科醫生告訴我:「Peter,你應該要讓自己變回有創造力的樣子,這是你能夠重新與世界對話、用顏料和畫布解釋你內心波瀾的機會,」相隔8年我才又重拾畫筆。

鏡:你是何時才意識到自己有亞斯伯格和過動症?當時是誰決定要讓你入精神病院治療的?
彼:我12歲上學時每天都站在走廊,每天老師都對我說:滾出去。每一天。真的是每一天,當這樣的循環不斷發生時,你連那一丁點對自己正向的感覺都會失去,會完完全全失去對自己的安全感。當時的我討厭自己的樣貌、討厭每件我在做的事。
當我終於厭惡自我到一個極限時,我跟父母說:我不想活了。是到這種地步我爸爸才在半夜決定:隔天起床我們會為你做些改變。我當時累壞了,他們從我的眼神看到空洞與倦怠。隔天醫生跟我父母談過後說:「不用回家了,你們幫他準備幾件衣服,他得即刻入院。」可想而知我當時的自殺傾向已處於非常危急的狀態。
自從我21歲入院治療後,醫生診斷出我有很多症狀,於是我開始服用藥物,他們一天給我60顆藥確保我的情緒穩定,但藥物又會產生一堆副作用。住院那一年最困難的還是當我與社會脫離,不能再見到家人、朋友,幾乎像是坐牢的罪犯,被排除在體系之外。那時期我的人生跟正常人有天壤之別,我從正常的生活中被抽離,不再是社會的一份子,而且24小時都被監視器監視著... …現在再回去看那段時光,我連一個星期都無法待在裡面,但當時的我就算被允許一週一次外出探視家人,卻仍總渴望回到醫院。在醫院的期間,我開始學習擁抱自己各個面向,無論是負面或正面的,試著去經驗這些真實的感受。
在醫院接受治療時我才又開始畫畫,因為那對我而言是相對容易的表達途徑,即使是團體治療時,我也是唯一被醫生允許可以畫畫的人,因為他們認為我能透過畫畫來釋放創造力,像是達到某種治療,藉此學習「我是誰」。直到現在生活都步上正軌,我還是時常跟我父母和妻子說,「我花了這麼多年讀書、到全世界探索自己、從事各種商業跟政治領域的工作,最後還是回到原點,才能認同我就是想要當一個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