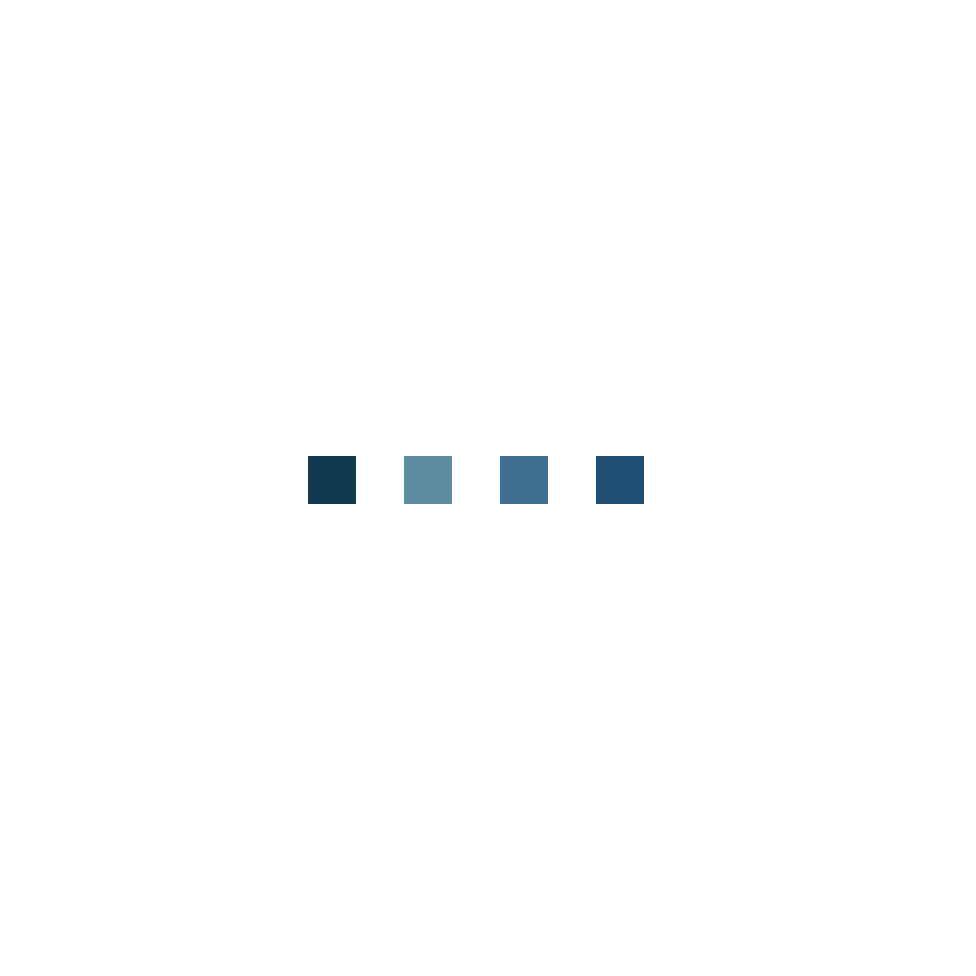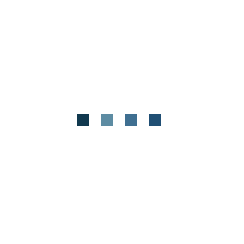廖偉棠書評〈並非不合時宜的紀念──《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全文朗讀

這篇文章在台灣刊出時,六四運動30週年的紀念已經過去一個月了,異時異地,讀者會善忘嗎?即使善忘也無可厚非,就像林慕蓮在《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 》「流亡的人」一章裡寫及吾爾開希在台灣的現狀,她的筆調對四周的冷漠不無諷刺,然而她們也不得不承認,如果無法跟本土議題掛鉤,流亡者並無理所當然的光環使他在一個民主社會中獲得持續關注。
按傳媒效應考慮,這篇文章應該一個月前寫,但現在寫,正是一個機會讓我們自問,我們能否做到像書中受訪者那樣拒絕遺忘?即使我們的健忘比起書中大陸人民的健忘更有合理性。或者說,我們拒絕遺忘有什麼必然的理由?
恰巧,閱讀這本書,追憶我自己曾在大陸親身經歷的八九六四的過程,與這幾天我幾乎一刻不停地從網路上關注的香港「反送中」抗爭運動的過程相交織,令我五味雜陳。後者鼓舞人心,但因為前者的經驗讓我始終抱有強烈的憂慮,因為這畢竟也同樣是一場文明對野蠻的抗爭。前者悲壯,但又因為後者的清醒讓我不斷認可林慕蓮的某些祛魅寫法。
未來的書寫者也許會學習她的書寫策略
閱讀中,我不禁提出這麼一個疑問:如果香港也發生鎮壓,30年後也會有人這樣抽絲剝繭地追尋沒有遺忘的人嗎?人們是否不會那麼容易遺忘抑或相反?網路時代貌似能留下更多的「物證」更多的線索,但它同樣容易風起雲湧稀釋掉很多即時的義憤,它的泥石俱下也容易縱容那些裝作理性中立客觀的偏幫,就像維基百科的很多條「爭議條目」一樣。
不過無論怎樣,我佩服林慕蓮的勇氣與策略,而我也相信即使香港淪亡民聲齊喑,未來也會有另一個林慕蓮去寫下今天的抗爭與拒絕遺忘的我們。未來的書寫者也許會學習她的書寫策略──林慕蓮非常從容甚至帶點幽默地接近歷史的步調,無疑比過往那種苦大仇深又混雜一種揭秘快感的「禁書」腔調更吸引人。
這也取決於她的特殊身份,她既是一位老練的西方記者,但也是一位中西混血兒,她的新加坡華人血統與香港的成長經驗令她對大陸的苦難依然存有悲憤,但點到即止,她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實際上也在「旁觀他人的痛苦」(蘇珊桑塔格語),從而不悲壯化自己的努力,只留下像「天安門母親」張先玲等守望者的務實身影,其實這更動人。
《重返天安門》第一章「小兵」不是從被鎮壓者,而是從一個間接執行了鎮壓任務的士兵寫起,有意思的是,這個沒有開槍的士兵,他拍攝了當年從軍隊角度看到的鎮壓,日後念念不忘,成為冒險創作六四主題藝術的藝術家。
無論身處境地如何,人都還是有選擇餘地的
陳光看似是一個絕無僅有的個例,國家暴力機器當中的覺醒尤其困難。據我所知,當年之所以從北京外面的窮鄉僻壤調配農村出身的「娃娃兵」前來鎮壓他們的同齡人,除了避免北京人不打北京人的尷尬,還存在這樣的洗腦──士兵們被灌輸這樣一種「階級仇恨」:你看這些學生,國家供養他們讀大學他們不珍惜,你們雖然讀不上大學但是你們愛國……
陳光自覺的藝術潛質讓他避免了這種洗腦,即使當時他沒有接受藝術訓練(退伍後他考上中央美術學院),他拍攝的現場照片就帶有一定的疏離和批判視角,比如說有的照片會把焦點聚焦在前景學生被摧毀的帳篷和雜物,而不是後面耀武揚威的同袍。藝術填補了良心的空缺,成為日後的良心。
無獨有偶,除了本書寫作時(「六四」25週年)站出來的陳光,除了著名的抗命將軍徐勤先,今年還有一位前戒嚴部隊軍官李曉明(曾是中國解放軍39軍116師的一名中尉)站出來。他們都說明了一點:無論歷史勝敗如何,屠殺當天角色如何,身處境地如何,人都還是有選擇餘地的,無論遲早、無論採取怎樣的形式,你仍可以選擇善與真。這令我稍微不那麼絕望,對人性。
林慕蓮建構人性的手段,是通過大量在政治話語和新聞報導裡會被忽略的「形而下」細節。比如她仔細描寫人民大會堂裡飢餓的士兵,他們被剋扣口糧(解放軍後勤無處不在的貪污直到前2年才被揭露),是餓犬的隱喻還是腐敗的極端呈現,林慕蓮留給讀者自己感受。
歷史漩渦中,每個人都有身不由己如被魔怔的時刻
她寫倖存的學生領袖張銘,目光不能從他頭上拔罐的痕跡以及他拔罐的行為移開,我們卻能從中意會:歷史的每個角色從高壓的政治空氣中吸入的毒素,拔罐也無法去除,也以不同形式流露於全書所有人身上,是一個共業。

除了關鍵的抉擇,歷史漩渦中,每個人都有身不由己如被魔怔的時刻。張銘作為學生領袖卻得親身體驗權力如何僵化和腐化,中國人的組織癖、開會迷同時也出現在抗爭者的陣營裡。張銘記憶中當時的人們自豪地攜帶寫著身份的布帶遊行,也是一直讓我不舒服的地方,抗爭成為一種炫耀,潛台詞是「連我作為《人民日報》、文聯作協這種國家喉舌的人都出來了」──鎮壓過後,最善於遺忘和改弦易轍的也是這種人,就和他們之前選擇成為權力附庸一樣輕易。
被林慕蓮採訪的每一個人都是讓人震撼的,同時也是存在特殊選擇角度的。選擇張銘而不是其他留下來的領袖,除了他的受難還有他在後八九時代的起起落落,他從商大獲成功但避免不了被清算,最後他絕食固體食物十年以上,與當年在廣場上的絕食構成一個迴圈,但有了更個人的意義。
同理,選擇吾爾開希而不是王丹,選擇張先玲而不是丁子霖,選擇鮑彤而不是其他趙紫陽的同黜官員,這種種可見林慕蓮的用心。她通過焦點的稍微偏移,實現對六四被神話化的一定程度的祛魅,祛魅不是摧毀,恰恰相反能令我深入一個時代最粗礪最本質的痛苦之中。有的時候,林慕蓮的筆很刻薄,但中國需要這種刻薄。面對悲劇,憤怒與感動是必須的起點,但單純的憤怒與感動無法推進我們對犧牲者與事件本質的理解。
不公平也存在於受難一方內部的沈淪中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本書的最後一章以極其沈重的方式觸及了一直被忽視的:北京以外的抗爭,尤其是非常慘烈的成都鎮壓。成都的意義何在?是徒勞的掙扎無謂的犧牲?還是匹夫之怒所證明的人性覺醒?那些在歷史的晦暗角落(比如鮮為人知的錦江飯店後院的刑場)裡消失的幽魂,究竟何時重見天日?如果缺乏了他們的同胞自己的努力,單靠外國人的見證和鈎沉足夠嗎?這種痛苦,林慕蓮讓我感同身受。原來不公平不但存在於善惡黑白兩分的對家,也存在於受難一方內部的沈淪中。
她知道不公平,但這本書的名字仍然只能叫《重返天安門》,而不是《重返一九八九》,因為天安門作為一個文化符號、視覺圖騰更容易喚醒我們的記憶,出版者也非常明白。這是不合時宜的紀念當中合時宜的「權宜」,我姑且也把這也視為整個悲劇敘事當中必要的一環,就像後八九時代的種種利益補償、花樣互噬、惡瘤增生,都是其綿綿不絕且聲聲漸烈的餘音。
「記憶的債越屯越高,最後得犧牲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人性──才能償還」書中最後這一句,怵目驚心,希望這不是這個苦難民族最終的宿命。
本文作者─廖偉棠
詩人、作家、攝影家。曾獲香港文學雙年獎,臺灣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春盞》、《櫻桃與金剛》等十餘種,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散文集《衣錦夜行》和《有情枝》, 攝影集《孤獨的中國》、《巴黎無題劇照》、《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