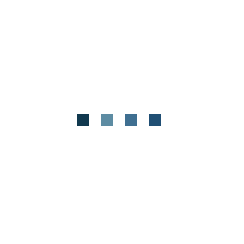她在馬來西亞看過成群神出鬼沒的長臂猿,在清晨大合唱;也看過飛鼠滿天飛;還有許多蜘蛛、螞蟻和青蛙。有時為了找一棵適合的樹,要在深山裡走上2、3天,最後一天才會搭起吊床。光是登山已經很疲勞,人在高空也沒有安全感,睡睡醒醒,只覺得夜晚很漫長。但她說:「我喜歡這種睡得很淺、對周遭高度敏感的感覺。」
有朋友能在樹上連續待72小時,把爐頭貼在樹幹煮食,吃喝拉撒都在樹上,只要有腰帶確保、脫下腿環和褲子就可以上廁所。但她認為獨自攀樹「最難的不是技術,是孤寂。」因此盡量選擇結伴上山,讓朋友在樹下紮營,而她在樹上過夜。

入夜之後,動物有時比白天還多,她看過山羌、山羊、飛鼠、麝香貓。昆蟲有趨光性,只要拿頭燈往樹上或地面一掃,蛾類的眼睛就像是碎鑽,散落在空中。「有時候在山裡,我覺得被凝視著,跟牠(動物)對望之後,我覺得我跟山的連結、對人生的熱情和動力又回來了。」
找路時不會想太多,簡單的路反而想很多
提起在山上摸黑趕路的經驗,她有時會關掉頭燈,擺脫燈光的侷限,藉著月光,視野反而更開闊。她說:「人在找路的時候不會想太多,反正就是要活下去。但簡單的路,反而會想很多。」想什麼呢?關於自己不擅與人相處。

「我說話很直接,容易得罪人。」陳雅得有回跟夥伴登山,但夥伴只帶GPS,沒帶地圖,她不留情面就跟夥伴槓上。但每個人對風險評估的標準不同,沒有絕對的對錯,所有人都平安下山,但陳雅得還是跟對方絕交。在福山植物園工作時,曾有同事不按實填班表,她認為做人該光明磊落,於是爆發衝突。但如今回想,應該有更好的處理方式。「這也告訴我,我不是自己以為那麼好的人。」那段時期,她每天走在森林中,一段之字型的陡坡,難度明明不高,走起來卻很累,後來她再走到同一段山路,總會想起當時的心情,「但同時,我又已經不是那時候的我了。那時候覺得天快塌下了,但過了幾年,人生原來還是很寬廣。」

陳雅得爬樹總使用繩索攀樹法,減少摩擦樹木,但也等於把生命託付於1條繩索,必須儘快上升,找到第2個確保點才能放心。從事攀樹的女性約僅占2成,陳雅得的風格強悍,有位男性朋友就說她的體能比他認識的9成男性還好,「根本就是戰鬥民族,不怕痛、不怕苦。」她遇到有刺的藤蔓,還會用手刀來開路。母親本以為陳雅得回國就是做教授、公務員,森林工作卻是沒錢又危險,也心疼她全身是傷。陳雅得無奈地說:「有一、兩次光是因為她看我傷痕,我就很生氣。」母女衝突不斷,但她漸漸理解母親的憂慮,「雖然淋雨、背重物、被螞蝗吸血會讓她擔心,但是我自己選擇做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