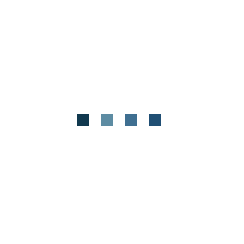米色飛鼠褲、酒紅色毛衣內搭藍色丹寧襯衫,坐在我面前的男人57歲了,然而皮光肉滑,身形消瘦,作少年打扮也擔當得起,唯獨他手上有一只老氣的銀鐲子與時髦造型極不相襯。前一天,他與作詞人李焯雄對談,不同的裝扮,佩戴同一只銀鐲子。想起他書中交代,童年時,母親在他手上戴銀鐲子,鐲子繫鈴鐺,他在屋裡走動,叮噹作響,母親便知道他身在何處。問手上鐲子可是童年戴那只?他說童年的鐲子在青春期早丟了,現在戴的,是後來移居荷蘭,母親送的,2010年,母親過世後再也沒拔下來,「小時候戴著鐲子,好像幫媽媽看著你,後來離開香港,沒有這個鈴,還是一樣的心情,不管你走到哪裡去,媽媽還是聽到你的,還是呼喚著你的 。」

香港樂壇寫詞人3大山頭,「林夕多情,黃偉文摩登,周耀輝另類」,眼前的男人是最另類的那個。1989年,他28歲,幫達明一派寫〈愛在瘟疫蔓延時〉入行,作品於兩岸三地發表,累積至今逾千首。他模糊情歌裡的性別,讓黃耀明〈忘記他是她〉;他令王菲〈色盲〉,「看到似雪的晚上,像日的月亮」,太熱了,太悶了,也幫張國榮高掛〈十號風球〉,「天氣差,更需要愛嗎?正下雨,而誰人護花?」林夕說:「如果用3種東西比喻我們,我是一塊海綿,黃偉文是一個刺蝟,周耀輝是一個雕塑,而且是紫檀木的,小葉紫檀,最貴那種,現在已經滅絕了。」
他們住在高樓
我們躺在洪流
不為日子皺眉頭
答應你只為吻你才低頭
〈下流〉
詞人年前來台北參加國際書展,台灣初登場並非談詩論藝,而是悼念母親散文集《紙上染了藍》發行繁體中文版。 母親病逝後,他在電腦上開了一個文件夾,「LONG LONG FAREWELL(漫長的告別)」,想到什麼就寫什麼,企圖用書寫頂住遺忘,「平常不用特別去看,但我知道我需要,或擔心遺忘的時候,它(文字)就一直會在,偶然的時候,晚上發夢,還會夢見媽媽。醒過來會很懷念,會拿起書翻一翻。」

寫作過程是這樣:粵語思考,紙筆寫下,隨後輸入電腦,因為用的是漢語拼音,所以得用普通話再唸一遍,曲折的家族歷史在迂迴的創作中變得更百轉千迴:母親原是廣東一戶周姓人家的女兒,少女時期搬進一處相熟男孩的家,跟著這男孩一家搬到香港,也跟著姓成,但後來與一個姓周的有婦之夫在一塊,生下周耀輝姊弟。這姓周的在香港經商失敗後,跟同鄉到溫哥華發展,和元配重修舊好,最後,只剩下周耀輝母子3人,住在黃大仙3坪的徙置區裡(低收入公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