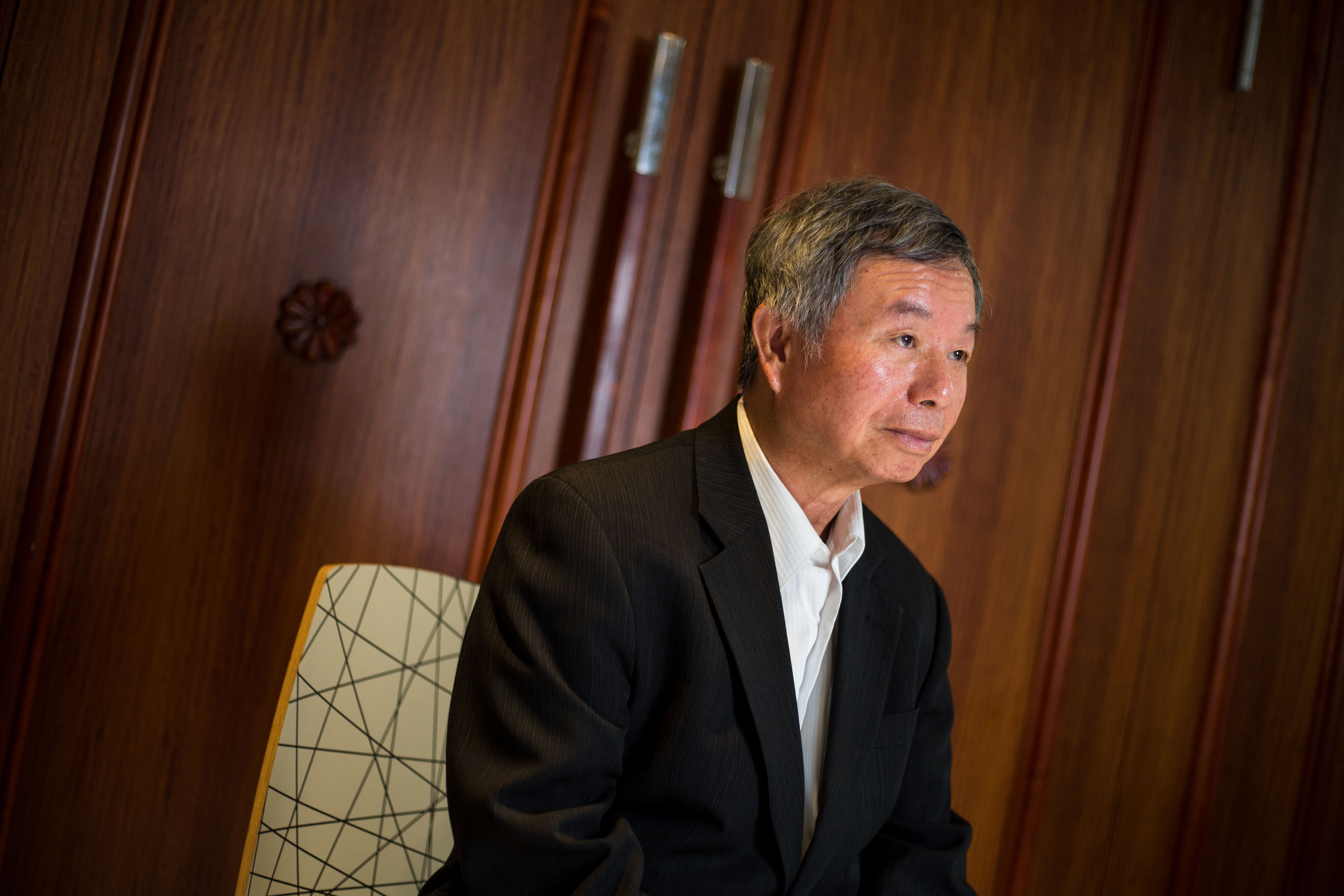楊志良提起大他2歲的哥哥,罹患大腸癌到後期,有天清醒,台北聯合醫院總院長黃勝堅剛好來看他,問他有什麼願望?楊志良的哥哥說,好想喝啤酒啊,在醫院喝酒簡直無法想像,但黃勝堅為完成病人臨終心願,找人去買了啤酒,讓楊志良陪哥哥小酌。楊志良說:「隔2天,我哥不吃不喝,在深度鎮定底下走了。我當然不捨,但是這跟安樂死有什麼差別?只是安樂死更積極一點而已。」楊志良認為,如果傅達仁當時有《病主法》,他只要預先簽署,根本不需要去瑞士。
安樂死是加工死,對家屬跟醫師都是心理創痛
楊志良解釋,依《病主法》如果有預立醫療決定,當符合下面幾種條件,醫師就可以依病人意願執行,第一,末期病人;第二,處於不可逆轉的昏迷狀態;第三,永久植物人;第四,極重度失智,第五,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的11種疾病(包括小腦萎縮跟漸凍症等10種罕病跟1種疾病),或痛苦難以忍受。楊志良特別強調「痛苦難以忍受」的標準,「這不是醫師認為,是病人認為。你看這範圍多廣,只要我有不可忍受的痛苦,這是主觀的,解釋是很寬的。所以我反對安樂死,安樂死是加工死,對家屬跟醫師都是心理上的創痛。但是,不要維生系統、自然死,執行的醫師跟家屬比較能接受。」
目前反對安樂死最激烈的就是醫師團體,除了風險考量,還有過往醫學教育的訓練都是「救人救到底」,怎麼可能去「殺人」呢?
什麼人需要安樂死?歸納2016年荷蘭跟比利時尋求安樂死的人罹患的疾病,癌症最多,超過六成,另外就是神經系統、心血管跟呼吸系統疾病、老年症候群、認知症(亦即失智症)及精神疾病等。江盛曾推估,台灣有安樂死需求的人,每年約有2千到4千人,但他們非老即病,難有力量發聲。
40歲的溫金盛活得痛苦孤寂,一直盼望能安樂死。
16歲那年,溫金盛騎車被計程車追撞成全身癱瘓,24年來,他大多時間只能躺在床上,唯一能跟外界溝通就是透過網路。多年臥床,他的肌肉萎縮,骨骼嚴重變形,心肺功能剩不到一半,清醒時全身都在痛。他覺得自己什麼都得依賴人,無法做想做的事,每天只能追劇、上網,活著根本沒有意義。更讓他愧疚的是,母親照顧他10年,因過勞早逝;父親現在也74歲了,人生三分之一都在照顧失智症的奶奶和他,如今也全身是病。
比利時聯邦監督評鑑委員會的一份報告記載了申請安樂死者面臨的各種痛苦,包括仰賴他人、失去獨立自主的能力、孤獨、絕望、喪失尊嚴與擔心失去跟社會接觸的能力等,全是溫金盛面臨的處境,但是溫金盛卻不知道還要承受這些痛苦多久?他說:「癌末病人還可以預期死亡時間,但是像我這種脊髓損傷的躺50年的人都有,我不知道盡頭在哪,很可怕。安樂死是我的權利,但是旁人覺得,我還呼吸,就該活著。可是這些人了解我的痛苦嗎?」

多年來,重度癱瘓的韓治偉也寄望台灣安樂死立法,讓他有條路好走。但是眼看自己身體惡化到連接受安樂死都快沒有能力了,又看到政府跟政治人物總是以再研議迴避問題,他轉而跟隨傅達仁申請到瑞士安樂死。
仔細翻閱韓治偉生前完成,但未曾出版的書稿,處處看到韓治偉跟生命的搏鬥。雖然從小罹患腦性麻痺,但他努力學走路,認真學習,到大學跟博士班旁聽特殊教育跟心理學課程。他也曾幻想有機會覓得佳人良緣,但是身體的持續崩壞,他終於明白此生是無可能了。
還有多少像我這樣沒有尊嚴的病友,繼續維持這所謂生命徵象
他的書寫到無法再用電腦為止,討論台灣諸多長照悲歌個案和對安樂死的想法,最後他在家人支持下,於瑞士完成安穩睡去的夢想。但是如他書稿所言,「還有多少像我這樣苟延殘喘,沒有尊嚴的病友們,拖著病體,對家人抱著內疚的心情,繼續維持這毫無意義的所謂生命徵象?」
的確,有多少人有韓治偉的經濟條件可以選擇到瑞士死亡呢?
安樂死是「人到底有沒有自主死亡權利」的拔河。
為維護憲法保障人的生存權,刑法有殺人罪專章,其中「加工自殺」跟「協助自殺」,都被認定觸犯「殺人罪」,最高刑期分別是7年和5年的重罪。最高法院庭長黃瑞華從此推論,「人如果有權自殺,別人幫助你就不是犯罪,這表示法律跟我們社會還是不允許自殺。」
但擁有英國格拉斯哥大學醫學博士,曾在馬偕教導醫學倫理的江盛則認為,環顧整個西方歷史,雖然因為宗教關係,一直不允許自殺,可是「人追求幸福,當這幸福受到疾病威脅時,我們還要聽那些醫師或教會給你的神話嗎?還是要回來聽聽自己要什麼?死亡是人的自由跟權利,整個人類都在爭取這件事。」
社會對自殺的汙名,推動安樂死的團體一直「尊嚴善終」取代安樂死,認為安樂死是「喜樂再見」,不是自殺。江盛卻有不同看法,「這種說法是對自殺的禁忌跟污名,請問安樂死不是自殺是什麼?」
交大科技法律所所長陳鋕雄認為,在生命倫理問題前,涉及的都是人對自己要做的事,國家要不要去干涉的問題,「安樂死就像墮胎,涉及個人的基本權利,如果國家要干涉,就要負舉證責任,證明這樣的限制是適當手段。」
檢視荷蘭跟瑞士相關法規,會發現荷蘭並沒有將生命自決權入法,而是將安樂死視為醫師的醫療權,醫師同意才能執行。瑞士為了不抵觸生命權,並沒有將安樂死立法,而是改變刑法對協助殺人跟加工自殺的解釋,認為如果是「利他殺人」不算犯罪,依此保護醫師合法執行安樂死,免於被依殺人罪追究。
許毓仁所提安樂死草案,也不認為人有死亡權利,而是讓法律賦予人死亡請求權,再由醫師專業跟一套法律制度去決議,是不是可以安樂死。
在傅達仁案裡,檢察官事後並沒有以刑法的「協助自殺」起訴幫助傅達仁赴瑞士的家人。江盛認為,檢察官是默認重症病患在必要時可以結束生命。對此,鄭貽說,他們無法猜測檢察官的想法,但是兩次赴瑞士前,都因害怕被阻止,不敢告知任何人。甚至有記者質疑傅達仁怎麼不快點去死,是在刷純在感嗎?讓他們很無奈。鄭貽說:「事前我們就想過可能要負的法律責任,但是既然是傅達仁的選擇,就這樣吧,我們一起承擔。」
一位不願具名的檢察官受訪時分析,不追究傅家人,第一是家屬幫助到瑞士就醫屬間接行為,不必然構成自殺,在行為因果關係上有爭執空間。第二是瑞士安樂死合法,我國對傅達仁的家屬和瑞士醫護人員都沒有審判權。「當然,最主要是,檢察官不會找自己麻煩,這種事情是個人選擇,又有價值爭議,沒有必要主動攬在身上。」
★ 《鏡週刊》關心您: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 自殺諮詢專線:0800-788995(24小時)
- 生命線:1995
- 張老師專線: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