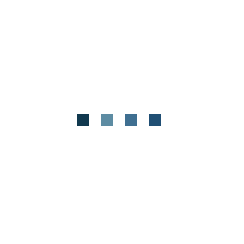阿嬤臥床2年多過世,紀岳良開始接觸安寧醫療。為了減輕末期病人生理及心理的痛苦,安寧療護著重症狀控制,給予緩解性的醫療照護,臨終也不會刻意急救。紀岳良覺得如果當初讓阿嬤接受安寧照護,她就可以不用插管好好走。不久,紀岳良的阿公也因嚴重失智吞嚥困難,幸運的是他在家斷氣,沒有經歷像妻子那一段折磨。
阿公阿嬤離世讓紀岳良開始思考,以後可不可以不要再經歷阿嬤後面那些事?兩年後,紀岳良的父親確診肝癌末期。剛開始,紀岳良的父親口服嗎啡,但是口乾舌燥、便秘,還會昏睡,意識不清,他吃沒多久就不願吃了。紀岳良說,父親說他不想「睡到死」,之後嗎啡改用貼的,也沒有改善這些副作用,他還是很痛。
痛在我身上,你們怎麼知道我的痛苦
看父親這麼痛苦,紀岳良嘗試找醫院讓父親接受安寧照護,但是台中有安寧病房的醫院不多,有也沒有家人陪伴的空間。如果住套房,一天要1萬塊,剛當律師的紀岳良覺得自己如果硬付,等父親走後大概也負債累累。
最後時光,紀岳良的父親待在家,紀岳良說:「他營養不良,出現併發症,無法走路,連話都說不出來,已接近失能狀態。他曾痛到跟我媽說:『我何時可以走?』他想早點解脫,如果那時台灣有安樂死的法律,我爸會選擇那條路。」紀岳良的父親不吃不喝幾天後,某天於夜裡斷氣。紀岳良說:「我從我爸身上看到,安寧病房可以做一些事,但是不可能解決所有病痛。」

傅達仁的太太鄭貽說,當傅達仁決定向瑞士尊嚴協會申請安樂死時,家人根本無法接受,用各種方式推託,延遲申請。傅達仁為此數度跟家人發脾氣,「痛在我身上,你們怎麼知道我的痛苦?」到後來傅達仁沒有嗎啡無法做任何事,甚至得靠嗎啡才吃得下飯。他曾跟來家裡的安寧醫療團隊說,「如果可以吃得下飯,我當然活啊,如果連最基本功能吃飯都失去了,那活著有什麼意思?」
傅達仁第一次去瑞士,看家人沒有準備好,兒子傅俊豪又在瑞士生病,他不捨拋下家人返台,但是一回台灣就因嗎啡過敏送急診。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躺在病床上,24小時不停的翻白眼,無意識的躺下、起來,讓家人嚇壞了。但是傅達仁卻奇蹟似的醒來。這次瀕死經驗痛撤心肺,讓傅達仁更確定要去瑞士,選擇無痛離開。家人終於也接受了。傅俊豪說,「父親生我時六十幾歲了,他從小就告訴我,爸爸有天ㄧ定會走。看著他一天天衰弱,痛苦地過每一天,我逐漸被他說服。」
有醫師認為,傅達仁如果接受安寧療護,不吃不喝,經過止痛跟鎮靜,可以安詳的走,並不需要安樂死。但是傅俊豪說:「父親是安寧緩和醫療的病患,可是安寧醫療對他來說,很像坐慢車,先是止痛藥一顆、兩顆、三顆;後面是嗎啡,從1週1瓶到3天1瓶,沒辦法有效止痛;嗎啡造成的暈眩也讓他很容易跌倒,因而更痛苦。當安寧醫療到了極限,我父親決定搭快車完成自己的善終。」
如果有快車,為什麼要叫我搭慢車
「如果有快車,為什麼要叫我搭慢車?」照顧母親的經驗,讓婦產科醫師江盛很認同傅達仁這句話。
2017年,江盛提早從馬偕醫院退休回家照顧父母親。沒想到回家就診斷母親罹患失智症。「她後來癱瘓,整天喊痛,我們決定使用止痛藥,但是我覺得這個止痛藥是不夠的。我媽還長褥瘡,她只要坐輪椅20分鐘沒拉起來,壓迫皮膚就長出水泡。」江盛說,他是外科醫師,就天天幫媽媽換藥,但是水泡到處長,他想盡辦法幫她換姿勢。江盛嘆口氣說:「但是睡覺時,大家都沒力氣啊,半夜怎麼幫她翻身?以前在醫院看到病人長褥瘡,會覺得怎麼會照顧到這樣子?當我照顧母親後,才了解照顧是多麼辛苦的事。我媽最後好瘦,我充滿罪惡感。這些都很困難。」

江盛的母親年輕時是護士,曾叮嚀江盛,她以後不要插管。到後來,江盛跟母親的主治醫師討論,只讓媽媽打抗生素跟點滴,沒有給她進食,江盛說:「因為醫師的訓練,第三天我就知道她死定了,當時我曾想,我是第4天就讓我母親死,還是拖到第14天以後死,但是我想我媽應該不會希望我替她這樣做,因而入獄或變成一個新聞人物。」看母親這麼痛苦,江盛甚至檢討一定是自己愛母親不夠多,否則怎麼忍心她承受最後苦難的11天?
江盛覺得,人的死亡變化有千百種、千萬種,安寧照顧不可能解決這一切。江盛也開始思考「如果我處在我母親那個局面,我會希望兩個女兒怎麼做?」江盛大女兒在英國當醫師,二女兒在波蘭唸醫學院,他不希望她們處在他當時的局面。「我必須為我的死亡準備。」2018年,他發起公投連署,希望安樂死作為一種臨終抉擇,能引起社會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