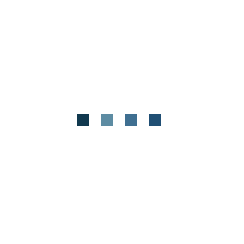楊雅喆
- 出生:1971年
- 學歷:淡江大學大傳系
- 代表:2008年《囧男孩》
- 作品:2012年《女朋友男朋友》、2017年《血觀音》(獲金馬最佳劇情片)、2021年《天橋上的魔術師》(獲金鐘最佳戲劇、最佳導演)、2024年《破浪男女》。
2000年,楊德昌拍《一一》,53歲。2001年,侯孝賢拍《千禧曼波》,54歲。2009年,蔡明亮拍《臉》,52歲。2015年,張作驥拍《醉生夢死》,54歲。2024年,53歲的楊雅喆也交出了他第4個長片《破浪男女》。
性欲是讓人活下來的欲望
「你不會看到有哪個像吳慷仁這個級數的演員,願意這麼犧牲去舔一個女演員的腳,還能一邊講話一邊舔,舔得很色情,腳明明不是性器官,卻讓他舔成了性器官…」訪談從吳慷仁舔腳開始,訪談逐字稿放到ChatGPT校對,螢幕屢屢跳出「此內容可能違反我們的《使用政策》」警示,「這是金馬獎導演的訪問,請你尊重專業,傻子!」對AI下指令,一次、兩次,但AI大概覺得自己被冒犯,索性把整個文件移除了。
然而電影也真的夠聳動,多P雜交、皮繩愉虐、膠衣性愛…劇情如片名,男男女女又浪又破。年過50的男人,破格拍出如此一部禁忌電影,官方說法是因當年拍《天橋上的魔術師》,10集影集等於5部電影,自己平生絕學全都使上了,太累了,想來點輕鬆的。但與我們訪問又改口,說創作核心不是約砲文化,而是性,「十幾年前吧,訪過一個領重大傷病卡的男人,遺傳性疾病,無藥可醫,他行動不便,還要養小孩,生活蠻拮据的,人生可能就這樣一路走下坡,然後躺在床上等死。生活最大安慰就是每個月存3,000去嫖妓…我一直想著那個畫面,男人搖搖晃晃爬上按摩院2樓階梯被服務,事實上,他也不可能有什麼性能力,但這樣一個付錢的女人卻能給他安慰,那時候我30幾歲吧,對性的概念都還只有爽,但那個人告訴我說『性欲是讓人活下來的欲望』,我整個人豁然開朗。」53歲的楊雅喆說,他拍新電影,無非想證明性欲等於生之欲。
繩縛的過程超像觀落陰
面前的中年男人瘦瘦小小,看上去粗獷,卻有「影后製造機」封號。編導的電視劇讓六月、謝月霞、萬芳拿金鐘獎,3部電影捧出梅芳、桂綸鎂、惠英紅、文潔4個金馬影后和女配角。其作品細膩刻劃女性內心曲折,然而精彩的心理戲在新片卻被赤裸的性愛場面取代,生理男何以有把握劇本中寫的女性性心理是真的?他說田調,田調,永遠是田調。田調是一個有戀父情結的高官隨扈,田調是一個藏在膠衣裡自慰的寂寞男人,田調是一個體面的返鄉創業青年,白天衣冠楚楚,晚上和哥們交換伴侶互尬。他說twitter音訊空間始終有敢露敢言的女生,做性愛賽後檢討。

「800個女生就有800種性高潮,讓我覺得性愛跟大海一樣,好包容好廣闊。我不會說我拍完這個片就變得比較成熟,但面對各式各樣的性癖好,至少會懂得不批判。誰不著迷於性?但這麼私密的事,得要先回到自身的觀察,然後看性可以帶你到多遠的遠方。」不對啊,你的電影類型不一,不約而同都出現藍領階層男性的意淫,莫非是自己的情意結?狡猾的中年人答:「我在寫劇本的時候可能真的放了我的祕密。但是呢,當一個樹洞藏了很多別人的祕密,祕密本身就不可信了。因為連我都分不出來哪些是自己的感受,或者是我田調而來的祕密。」

中年男人唯一招認的是電影中女人被繩縛的情節是親身體驗,「劇本寫女主角被綑綁,監製問:『你有沒有想過被綁女生的心情?怎麼不去被綁一下?』我想也對,找了個繩縛師來綁我。欸,超好玩!在被蒙眼幾近無聲的狀況下,我可以幻想劇本走向,被綁的女生、綁人的男生在想什麼,那過程超像觀落陰。被吊起來的身體旋轉著,超性感、超刺激,那不是讓你勃起或下面濕這麼簡單的事,你的感官都被放大了,甚至聽得見繩子轉動的聲音,逼哩逼哩。電影中有一場戲,女主角眼睛被矇起來,被男生壓在窗前從後面來,男生突然把窗簾掀開,窗子打開,感官一下子被放大,那場戲都是從這個經驗而來。」

露水姻緣也是緣
海報文案露骨地寫著「uberdick(外送屌)帶你上南天門」,然而陌生人的性也帶人下地獄。星座專家唐綺陽看完爆哭,說:「楊雅喆到底是多想逼死人?電影都是死裡求愛的一群人啊!」他彷彿人類學家,幫觀眾田調網路世代的性生活,他同時也是觀落陰道士,把觀眾打入性愛的阿鼻地獄。然而就算死了也要愛,「性沒有那麼簡單啊!如果,大家可以反覆追求它,跟不同的人做100次、1,000次,你到頭來一定會想,我重複這1,000次,到底為了什麼?」他自問自答:「露水姻緣也是緣。哪怕約個一次、兩次的砲友,都有可能為你人生帶來新的困惑,那並不是因為他騷擾了你,而是你被他撩動了之後,你看見了自己的問題。也有可能因為這樣子,你記得了某個人的溫暖。」

他從2020年《天橋上的魔術師》拍攝中後期開始構思故事,劇本在腦海中想很久、電腦前寫很久,但拍的時候又拍很快,去年4月中旬開鏡,5月底殺青。電影開拍正值台灣#MeToo運動風風火火,故事太冒犯,演藝圈捅紕漏的也不少,不怕被炎上?「國外電影圈這幾年興起『親密指導』,台灣腳步跟得蠻快的。《血觀音》大尺度床戲是我設計的,那時候又要拍得性感,又要顧及普遍級尺度,拍得很挫敗,但現在就交給專業的來,這些親密指導多半是舞蹈家出身。我說我想要這場戲很獸性,他們建議騎乘式體位,導演的指令、演員能露點露到什麼程度,全由他們居中協調,都是契約化的過程。拍攝時,只有演員、攝影師和親密指導在現場,我只在隔壁的房間,透過monitor螢幕觀看,一切都變成標準的流程了。」
楊雅喆自嘲是控制狂,拍《天橋上的魔術師》很會哄小朋友演戲,然後轉過頭,又拿小朋友演出片段給成人演員看,說:「他們表演的純度在這裡,你能拿那個摻水的東西來騙我嗎?」過程來來回回非常消耗,但拍新片學會放鬆,「我懂得放手,讓專業的人來,必要的時候再勒緊他們。是,我綑綁別人的技術升級。」繩縛和拍戲,他用的是同一套修辭。

又或者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分工越來越細,意即台灣電影產業越來越健全?「可能是和中國關係劃清楚之後,想去的人就去,不去的人就留在這邊找一碗飯吃,留下來的人非但沒餓著,還能體面地、好好地把飯吃完。」話題還是回到政治了,放眼檯面上的導演,沒有比他更激進,更喜歡在網路上靠北時事,「我自己也會想新電影要走宣傳了,是不是該謹言慎行一點,但如果我的電影是對於性的探索、對自由的追求,結果自己的態度是這樣保守,幹,那我也太人格分裂了吧?」
訪問當天正值立法院外的青島東路風起雲湧,我們討論訪問告一個段落,是否就去衝一波?「我還是會去遊行,但現在已經不會站在台上講話,我喜歡淹沒在人海裡,享受自己就只是人群10萬分之一的感覺。如果上台講話,就沒有那種跟大家站在一起的感覺了。」
大腦才是真正的性器官
確實,數天後我們約在樂華夜市拍照,他的草莽氣質彷彿賣雞排的老闆,或路邊吃三鮮羹的男人,完全融入人群。他的導演前輩同行,多的是優雅的中產階級,吃穿用度見識不凡,唯獨他還在永和租老公寓,屋子堆滿雜物,簡直是倉庫。他的生活動線就是租屋處方圓五百公尺,《血觀音》還是在4號公園的圖書館寫的。他家養了一隻12歲的貓,貓幾歲,他就在這裡住了幾年,但他說,這可能是他人生最後一次養貓了,再老些,每天扛著貓砂,老公寓爬上爬下還是很累的。

聊起那些與他年紀相仿的同行們,皆已攀過創作生涯的一個山丘吧,然而有人時不我予,有人滿手資源,問他可有中年危機?「無時無刻啊,但我常常想到克林.伊斯威特。他有創作匱乏嗎?肯定有。但他沒在乎獎項、票房,一直維持很好狀態,我希望我可以像他那樣拍到80歲…」他說大腦有在動,努力創作就不易老,稍早問他,中年男人的性難道沒有力不從心的時刻?「你要讓你的大腦運作起來。大腦才是真正的性器官不是嗎。」性欲、創作欲,對他而言,都是同樣的譬喻。
我們在暗巷兜兜轉轉,找拍照景點,6月的夏夜雖然有晚風吹拂,但風是燠熱的,他說前一陣子去運動中心游泳,本來他是不吃冰的,但想到5月初過世的媽媽生前愛吃霜淇淋,基於某種補償媽媽的心態,連續吃了3支。

家有白事,中年人碰到電影跑宣傳,也得裝得若無其事,「入殮的時候,我跟我妹本來都有要給媽媽穿的衣服,兩個人都堅持各自挑的衣服才是媽媽的品味,討論不然擲筊決定好了,幹,擲出來都是笑筊。後來我想到她臨終前幾天,我用手機播妮妃雅變裝皇后奪冠的影片給她看,請外傭從衣櫃裡拿出一套大花大綠的衣服,問她是不是想穿這套?果然是聖筊,我媽到頭來就變成一個超炫的Queen了。」
會拍電影是幸運也可能是不幸
百無聊賴的生活中,唯一的安慰是新養的一盆新幾內亞蘭花開花了,那可是全世界少數會綻放香氣的蘭花。話題繞回蘭花,他說很多年前,有人把枯萎的蘭花丟在天臺,他不捨,帶回去澆水,澆著澆著,花活過來,1盆、2盆,養著養著,現在有3、40盆,講起蘭花的交配和培育,疲倦的語氣有了起伏。
「蘭花啊,就算是相同爸爸媽媽,開出來的花也是不一樣的啊,就像我會拍電影,就可能是爸爸媽媽把一部分好的基因留給我,我會拍電影,可能是幸運的,也可能是不幸的,現在家中有的沒的事,都變成我要負責了,剛剛你問我對『五十知天命』的看法,我想大概就是這樣吧。」
講蘭花、講新拍的電影,講自己的人生,性欲等於生之欲,或者對他而言都是同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