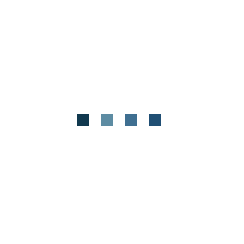里長說阿金(化名)的房子裡曾死過3個房客,有次警察還在屋外拉起封鎖線,左鄰右舍全圍著探頭探腦。里長擔心他老租給一些「怪怪的」人,遇上崔媽媽基金會帶人來看房時,會湊上去告誡「你們要篩選一下啦,不要再租給奇怪的人了。」聽到里長這麼說,阿金心裡直嘀咕,「已經篩選過了啊。」
如今的房東 也曾是苦過來的房客
那是阿金買的第一棟房子,1970年代華中橋剛剛通車那時入手,獨棟兩層的樓房,再往上加蓋兩層,每層只有一戶。本來是要買給兒子住,但兒子嫌坪數太小,每戶才8坪左右,1天也沒住過,後來專用在出租。
第一個過世的房客,住了12年。房客早年在做捷運工程,捷運完工後,收入也跟著不穩定。「他最初付房租,一口氣給半年,後來改成月付,再後來斷斷續續地給。」

最後幾年,房客生病住院,阿金常去探望,拖欠的租金阿金也不催,只要他好好保養身體,「他跟我說他有交代弟弟房租的事,後來人過世了,我跟他弟弟提起房租,對方說不清楚,我也就算了。」停頓一陣,阿金補上一句:「嚴格說起來,他不是死在房裡頭。」
或許是因為阿金也做過工程,能同理同為做工的人。阿金的老家在十分寮,30年代,十分寮還是煤礦坑,阿金認識的每個人都靠礦坑維生。小時候上學前,他會先到礦坑推煤礦賺外快,「推一趟到火車站,再去上課。」有次同伴沒注意,讓推車壓住他的手,小指就這麼斷了,「一開始不痛,過幾分鐘血一直冒出來,才知道痛。」
國小畢業後,阿金到台北的紡織廠當學徒,「我不想留在礦坑,太可怕了,以前幾個班上的同學在礦坑工作,早上還看到人,一小時後『碰』一聲,人就這樣死了。」在紡織廠當學徒,每個月有60塊零用錢,剩下的碎布師傅還會幫孩子們做成新衣服。
當完兵、結了婚的阿金和妻子租屋在新店,緊鄰著瑠公圳,阿金跟著台灣經濟發展的腳步,繼續待在紡織業,紡織業沒落後,阿金進了電子廠,也做過工程;最苦的時候,阿金也曾當過清潔,去掃廁所,「有時沒工作,房東會叫我們夫妻倆跟他一起吃飯,貼他幾塊錢當飯錢就好。」房東做木工,有工作時也會找阿金一起去做。
陸續攢錢買下第2間、第3間房後,阿金開始出租。和其他人一樣,阿金最初也到處貼紅條子招租,「但亂貼被抓到,1次罰1,800元,很貴。」
弱勢、罪犯和精障 都曾租過他家
1989年,無殼蝸牛運動號招夜宿忠孝東路,因著運動而生的崔媽媽基金會隨後推出租賃服務,媒合房東房客,「我那時覺得這樣很方便,不用到處貼紅條,委託他們找房客就好。」那時起,阿金成了崔媽媽基金會合作30年的友善房東,出租房子給弱勢房客。
第二個過世的房客,便是崔媽媽轉介的房客。大部分的時候,房客總是很客氣,但一喝酒變便換了臉孔,「喝醉常常半夜打來罵人,罵完隔天酒醒他自己就忘了,問他幹嘛罵我,他又會很客氣地道歉。」阿金苦笑,怎麼勸說也沒用,房客身體不好,但老愛喝酒。有時阿金也會跟崔媽媽基金會埋怨房客喝醉的模樣十分惱人,但埋怨完仍是繼續租給對方。
有天接到電話,話筒那端急著要他去開門:「轄區員警說我房裡死人了,檢察官要去驗屍。」阿金到了後,聽見圍觀的鄰居交頭接耳,「說『死人了、死人了』,我說:『死人怎麼了?』」房客過世後,房子打掃一番,還是交由崔媽媽基金會協助出租,媒合給弱勢房客。
第3個過世的房客,是個五十多歲的女性,同樣透過崔媽媽基金會媒合承租。房客曾在日本求學,後來因疾病而失業,「但她很上進,說要參加進修課程,之後去找工作。」只是才說完要去上課,隔幾日卻在家中過世了。
這次警察在門外拉了封鎖線,鄰居更在意了,崔媽媽基金會因此找來法師道士作法,讓鄰居安心。
除了過世的房客,阿金的房客中也曾有過精神障礙者、因刑事案件遭逮捕的、還有會惡意欠租,把牆壁打破一個洞的。許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弱勢房客,阿金倒是包容。他理解社會身份上的弱勢,難免伴隨各種問題:欠租、酗酒、生病、失業,他自己也曾是一名房客,也曾窘迫,當年依著房東的善意,才有機會維持住日常生活。
而且現在的阿金也沒有多餘時間分神處理房客的疑難雜症,阿金的妻子已中風多年,躺在床上需要人照顧、陪著去復健;兒子年輕時情傷後罹患重度憂鬱症,一度住院療養,現在才能慢慢能生活自理,偶而去發傳單、舉牌打打工,「我一個人要照顧3個人:太太、兒子和外籍看護。」對他而言,崔媽媽基金會的社工會時時觀照著房客狀況,房子的事全權交給基金會,讓他省下不少精力能陪著家人。
包租代管 房東依舊挑房客
阿金這樣的房東,可說是崔媽媽基金會合作對象裡的至寶,崔媽媽基金會居住扶助部主任馮麗芳感慨,願意成為友善房東的人本就稀少,且有些友善房東雖願意把房子租給弱勢房客,但同時他們對於弱勢會有一些「想像」,「有的人想租給單親媽媽,幫助對方重新站起來。但個案的狀況和這樣想像其實有落差,所以真的接觸個案時,房東的疑慮又會很多,媒合上一直有難度。」

2017年內政部推出「包租代管」政策,透過政府委託租賃業者擔任「二房東」,和房東簽下3年契約,再由業者一手包辦出租、管理等業務。「包租代管」看似省去了房東的管理成本,又保證3年內月月有房租收益,應可增加對弱勢房客的包容度。
但實際上面對弱勢租客時,房東內心仍有好幾把尺,「我們都會先篩選過一輪,像是付租金比較不穩定的,就先不幫忙媒合,因為我們還是擔心房東受不了,最後乾脆不合作,這個資源就斷了。」馮麗芳說,但到了房東那一關,又會再有第二波篩選,「有些房東會要求業者不要租給年紀大或身障的房客,導致最終媒合依舊不易。」根據營建署統計,截至去年中,「包租代管」媒合戶數達4,223戶,距離1萬戶的目標只走了一半。
且1萬戶的目標裡,提供給弱勢身份的戶數僅有4成,其他則留給一般戶。2011年內政部住宅需求調查報告中,六類經濟與社會弱勢中,無自用住宅者共有39萬4千多戶,弱勢居住的需求之高,但「包租代管」裡供給弱勢承租的僅有4,000戶,「區位好、租金實惠的房型一下就被搶空。其他6成提供給一般人的,我們想租也租不到。」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呂秉怡苦笑。當初希望增加弱勢租屋機會的美意,反而打了折。
專門服務遊民的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也曾想透過「包租代管」為手上個案找到家,「但我們的個案多是獨身一人,『包租代管』的房型比較偏向整層住家,這種房型租金又會比較高,就算扣掉補助,我們個案還是租不起。」芒草心協會秘書長李盈姿無奈道。
李盈姿說,他們也曾嘗試先讓一個個案透過「包租代管」租下1層3房的住家,再找其他2個個案合租進去,「但承租的那個人就很慘,要一直去催房租,另外2個人也會一直避不見面。好幾次都是承租人自己先墊。」
稅賦優惠誘因低 難吸引房東上門
去年底內政部推出「包租代管」第二期計畫,目標設定在媒合1萬5,000戶租屋。但呂秉怡並不看好,首先是房東對於弱勢房客的刻板印象並沒有消除,以崔媽媽基金會來說,因為配有社工協助處理個案狀況、連結社福資源,房東對弱勢房客的疑慮稍能緩解。但內政部的計劃裡並沒有要求業者一定得配備社工,成為房東和弱勢房客間的橋梁,因此在提升房東意願和包容度上效果有限。

且租賃市場裡,房東不願意曝光仍是最深層的問題。「雖然房東加入『包租代管』,出租的房子房屋稅、地價稅能得到減免。但是任何減稅政策,法律規定每5年要檢討1次。」呂秉怡說,房東擔心優惠稅率只是暫時性質,可一但成為合法房東,國稅局便能一直追查租金收入,未來得要多繳稅,因此多半不願參加。當政策無法翻轉長期地下化的租賃市場時,政策本身的效果便受到極大限制。
「歸根到底,我們要思考的是,包括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等政策,到底是住宅還是福利政策?」呂秉怡分析,真實的市場裡,就是有一群人因為身份和經濟狀況,既買不起更租不到房,但是當政策只是創造另一個租金相對低的次級市場,可同樣的排擠邏輯仍在其中運作,那萬千樓房裡,依舊沒有一處是弱勢房客的家。
★鏡週刊關心您:未滿18歲禁止飲酒,飲酒過量害人害己,酒後不開車,安全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