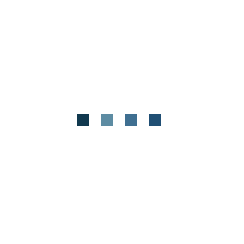院內寫日記 當成是遺言
當然不是為了省那6萬元。彼時在兒科急診擔任醫師的他,發現感染源就是從急診室出去的,「但我在那邊看診1個月以上了…所以我是為了保護家人,我如果不回去(醫院)的話,就要去找旅館。」他在和平被封住的院內,整整10天與世隔絕,只能寫日記每天報信。隔絕的日子,沒有一天睡好,「我是睡健保房,6個人1間,簾子拉起來,在病房裡面做隔離。因為沒有空調,很熱,戴著N95睡覺,早上起來,才發現口罩掉到床底下了。」17年來,他再也走不進去和平醫院,偶爾仍做著睡到一半口罩掉落的夢。那些日記仍留在網路上,像是這場疫情最初的碑文。他告訴我們:「那時是真的當成遺言在寫。」
遺言的內容,或可簡述為孤島紀實,雖然這孤島的意象絕不僅止於他的日記內容。孤島有層次之分,首先,台灣是國際的孤島,加入不了世界衛生組織;再者,和平醫院在台灣也被視為疫情重大災區,林秉鴻舉例:那時和平院內病人一度有機會被分流送到新竹署立醫院,結果車子到門口,當時的新竹市長林政則就出現了,率眾以車輛擋住急診室通道,「所以根本沒辦法解決和平封院的狀態啊。」

出院被歧視 鄰居閃躲她
最後,是院內的人,也為防疫而保持距離。同桌吃飯就是「很NG的行為」,露出口鼻時大家就各自躲開。體溫定時量,林秉鴻曾聽聞有清潔工因害怕而吃退燒藥壓制發燒。他同時透過新聞放送,看著這一切混亂,覺得像是末日。
當隔離結束,醫護從末日逃回現世,卻大多逃不了歧視。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副主任郭淑柳,當時服務於國泰醫院負壓隔離病房,身為醫護,其時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需要大量支援,國泰索性把整個7樓改成負壓病房,5樓成為醫護人員的隔離住所。她匆匆入院,以為是短期旅行,結果是長期抗戰。
從4月到7月,春天到夏天,郭淑柳就這樣和20幾位護理同仁被放在醫院臨時隔出的空間裡。當時的醫療體系崩毀了嗎?「算是吧。3層樓說封就封,大家也不敢看病。」心理上的隔離最令人難受,院外平時做醫護人員生意的店家得知醫院收治SARS病患,竟拉出白布條抗議,覺得醫護都在散播病毒。不甘心嗎?「有一點點,但你會知道,他們是非常恐懼的。」
受訪的醫護大抵有這樣的經驗。黃露萩的外甥女曾對她說:「舅媽,我好朋友都不跟我玩了。」小女孩的同學盛傳:「她舅媽在和平醫院工作。」大疫過去了,她卻沒朋友了。黃露萩回憶,有同事一回家,發現整棟鄰居每戶門口都放電風扇,對外吹,還有人直接把風扇對準同事家的門。
染煞的鄭鈺郿撿回一命,從新光出院後,還是要回診,她都穿著防護衣。每回救護車來接她,抬起頭,「就會看到鄰居全都站在陽台看。可是你心裡知道情有可原,那個無知恐懼…我們必須知道,他們的害怕是正常的。因為人性就是這樣嘛。」
趙月虹結束照顧SARS病患後,她在家中隔離,天天有里長、衛生局、警察用監視器確認,或親自登門按鈴,但這些人一走到樓梯口就止步,沒人願意靠近她家。她每個月拿給公公月俸26000元,讀幼稚園的女兒悄悄說:「阿公用酒精一張張擦拭鈔票。」
國際處境尷尬,台灣在防疫關口也難以擺脫被遺棄的宿命。台灣一直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問璩大成,抗煞當下,有感受到被世界遺棄嗎?他不談當年,但樂觀表示:「我們從自己歷史教訓逐步擴充能量。我們自己的國家自己要救啊。」「很顯然,我們(現在)建置的這些機制,都不是跟WHO學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