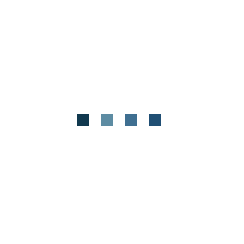電影院內觀眾的呼吸聲越來越沉重,搖晃晃的鏡頭對著全身赤裸、僅有私處打上馬賽克的越南籍失聯移工。警方正在對他大吼,但他似乎沒有聽見,或是聽不懂,他神色恍惚,企圖逃離警方的追捕,跑出河岸草叢,靠近無人的警車,與觀眾只剩一步之遙。槍聲乍響,子彈一發接著一發射進他背部腰臀與大腿,一連九槍,他從駕駛座滑落跌坐在砂石地上,鮮血汨汨從他的身軀流了出來,他意識恍惚地蠕動爬行,連聲哀號都沒有。
2017年8月31日,27歲的越南移工阮國非在新竹縣鳳山溪畔遭警方連開九槍致命,引發社會輿論。5年後,這段來自執法警方身上所配戴的密錄器影像,在紀錄片導演蔡崇隆最新作品《九槍》中首次公開,完整呈現阮國非中槍至救護車到場的半小時,第一台救護車先護送明顯沒有生命危險、只有鼻梁受傷的民防,圍觀的警察與民眾盯著阮國非在地匍匐,卻沒人敢接近,直到第二台救護車到場,警察將垂死的他拖出車底,在他肩上又踩了一腳,才將他弄上擔架的過程。震撼內容使其拿下2022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更被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評為當年最痛苦的電影。

蔡崇隆小檔案
- 出生:1964年
- 現職: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紀錄片工作者
- 學歷:政大法律系、輔大傳播所
- 重要作品:《九槍》《島國殺人紀事》三部曲、《公娼啟示錄》《奇蹟背後》《我的強娜威》《再見可愛陌生人》等
- 得獎紀錄:《九槍》獲2022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多項作品曾入圍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台北雙年展、卓越新聞獎專題報導獎等
紀錄社會不公 觀點犀利
電影放映結束後席間一片沉默,58歲的蔡崇隆走向台前,靜靜看著台下反應,就像這也是紀錄片的一部分。他站得挺直,面頰削瘦,戴著會變色的細框眼鏡,給人不苟言笑的第一印象。5年前,他從新聞得知阮國非事發身亡的消息時,便充滿了困惑:「為什麼警察抓一個移工會開九槍?事情究竟怎麼發生的?」而決心挖掘真相。
從早期擔任新聞記者到紀錄片導演,三十多年來,蔡崇隆一向將鏡頭瞄準社會不公義之處,觀點直接、犀利,包含為蘇建和、盧正等死刑犯平反的《島國殺人紀事》三部曲、聲援RCA女工抗爭的《奇蹟背後》等。這些年,他則多與原籍越南的妻子阮金紅合作,二人扛著小型攝影機,四處拍攝移民移工議題,有紀錄新移民女性婚姻觸礁的《失婚記》,也有追蹤在台灣淘金失敗、淪為失聯移工的《再見可愛陌生人》;二人共同經營的空間「越在嘉文化棧」,更是中南部越南人社群交流的重要據點。
即使擁有豐富移民工社群的人脈與拍攝經驗,調查過程仍然漫長。這幾年,蔡崇隆造訪阮國非住過的宿舍、訪談接送這批移工的白牌車司機,詢問遠從越南來台灣抗爭的阮國非的妹妹和父親,參與此案的法庭審理…他發現阮國非跟多數移工相似,卻又不同的地方,「慢慢這個人的形狀出來,他跟之前接觸到的移工不一樣,越在嘉文化棧假日移工會來聊天、吃飯、喝酒,會自得其樂,但阮國非看起來都很苦悶,臉書是各式各樣心情的感嘆,他在忍耐,受苦都不知道…」
拍攝靠做中學 過分投入
蔡崇隆團隊翻譯阮國非生前的臉書內容包含:「從現在開始,對我來說,星期天不存在了,星期天就和星期一沒兩樣,只要上班,不想休假。」「我在人行道上不斷徘徊,不知道今晚該往哪裡去?」「如果有一天,我在人生的路上跌倒了,媽媽,請原諒我。」有次,他還只寫了一個「苦」字。
「這批在工地(非法)打工的人,高勞動密度,沒有情緒出口,喝酒、吸毒,我覺得都可以想像,」靠著長年深入司法議題的人脈,蔡崇隆取得完整的密錄器內容,發現殺死阮國非的不僅是那9顆子彈。
他獨自在房間裡打開密錄器檔案,看到畫面的心情跟多數觀眾一樣,震撼、困惑,又憤怒,「不知道開槍是這樣開的,像射擊遊戲,後面他們(圍觀者)在鬼打牆,不知道在等什麼(不送醫)?但我又很同理他們,那種無視的態度,生活裡面就有了,我們不承認那是歧視,」阮國非中槍後,眾人與他保持距離,有人朝他喊「再囂張啊」,開槍警員也頻頻提醒後到者「他有攻擊性,不要靠近」;回想到此,蔡崇隆忍不住激動反問道,「今天對一個受傷的狗,都不見得這樣吧?狗很危險,會咬人,大家撲過去想辦法,但是他是個人啊?」

初訪時,我跟蔡崇隆約在他任教的中正大學傳播系教室,他的眼鏡因為日照,有些灰撲撲的,先前特映會上板著的臉,此時看來很悲傷,「其實我連看第2次(電影)都很痛苦,正片首映場看過一次,後來播都沒有進去看,桃園場我才又進去看,聽了那個歌,很多情緒又上來,邊講邊哭,前5分鐘沒辦法講話…」他淡淡地說。
阮國非生前壓抑、獨自承受生活的痛苦,蔡崇隆很能同感。大學念法律、研究所念傳播理論的蔡崇隆,畢業後短暫擔任報社文字記者,便進入商業電視台做專題記者,接著到公視拍攝紀錄片;因為不是本科生,他靠自己做中學,十幾年來馬不停蹄工作,曾經3年拍八支紀錄片。他渾然不覺自己過分投入工作,超出負荷、過勞,婚姻也出了狀況。
幼遭制度壓迫 個性敏感
「那是我最糟糕的時候,雖然產量很大,但狀況很不好,錯在我,我有了第三者,又採取隱瞞、拖延的方式,被發現時就變得很嚴重。我(當時)對感情的態度有點天真,一方面很累,不想面對…」直到他嘗試與前妻重建關係,已經覆水難收。2000年初,他搬離住了20年的台北,辭掉公視工作,在中南部三個學校擔任兼職教師,「我們兩個人都傷得很重,整個人生就那段最痛苦,離婚打擊很大,處在一個不太知道以後會怎樣的狀況…」
蔡崇隆在彰化市長大,但這趟並非搬回老家,而是在離家50幾公里的二水鄉找了個三合院,單身一人住進其中的廂房。在這個產米、不認識半個人的小鎮落腳,他直言沒有特別原因,只是搭火車通勤時發現此處風景優美。長達五年,他幾乎與外隔絕。偶爾接案拍片,有台北的工作,就睡紀錄片工會的辦公室沙發,省旅館錢;平時便一個人在村子裡晃,「晚上睡不著就去田裡看稻穗,騎腳踏車,練練瑜伽、打太極,那段時間可能對我的修復有點幫助,之前比較沒什麼空間獨處…但是我彰化的老媽媽不知道我的狀況,我沒有跟她講,」他乾笑了二聲。

「她知道了,一定會叫我回家住,我就不想回去,回家基本上就不用出門了,她做東做西給你吃,一定會有一個豬心塞人參…我媽其實已經很老了,我不想違逆她,但就是不自由,」這樣的情況過了幾年,他忽然接到媽媽的死訊。幾天沒聯絡,獨居的媽媽在洗澡時摔跤,就這麼過世了,鄰居注意到,才藉著警方通知到孩子們。「心裡很亂,很自責,會想說如果我有回去看看就好了…」蔡崇隆很少提及這段經歷,語速漸漸慢了下來。

「我本來就是比較敏感的人,對人的痛苦感受較深…」將紀錄片鏡頭面向弱勢與受壓迫的人群,與蔡崇隆的成長背景有關。小學時期,他曾因為不寫習作,遭受老師長期體罰羞辱,處罰方式包含打巴掌、打屁股、青蛙跳、原地半蹲、罰跪;升上國中後,他受升學主義影響,拚命念書,沒交到什麼朋友,常常熬夜讀書到1、2點、渾身無力上床,日復一日,「比較懂事了以後,會覺得這是一種制度的壓迫,到媒體工作後,還是看到很多這一類的事情,只是在不同領域而已。」

為無力者發聲 反思探問
面對壓迫或苦難,有些人能直接反抗衝突,但蔡崇隆不是,「應該也是膽小,我不願意這樣做,陽奉陰違是我成長的方法,我不喜歡彰化、不喜歡升學主義,爸媽的期待我也不太接受,但我基本上、外貌上符合你的要求,要考大學,我就認真考,但我都填台北,藉這個機會溫和地離家出走。」他淡淡笑說,法律系畢業後,他也曾應付父母考過書記官,但他根本不想當公務員,加上沒準備,自然落榜。
蔡崇隆的父親很早就過世了,是40年如一日的公務員。父親養了2個家庭,蔡崇隆是後媽的兒子。記憶中,同父異母的大哥會來拜訪,幫一家人拍照,送弟弟們禮物,「我爸有2個家庭,7個孩子,照理來說他應該收入不差,但經濟負擔很重,我都看得出來。小時候媽媽常跟他爭吵,後來好像大老婆過世(他們)才登記。」

過去,他畏懼自己成為像父親一樣的人,活得辛苦、沒有選擇;但走在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他知道自己不再是無力者,「我做記者、紀錄者,知道有這樣(無力)的人存在…有時候其實很單純,我對這個東西(議題)很好奇,想知道怎麼回事,想讓沒有機會講話的人講話,我不覺得在幫他,因為我也不想要被壓抑,也想要自由。」
《九槍》除了1/3為密錄器畫面,其餘則是透過模擬阮國非亡魂所建構的靈魂視角,走訪台灣各地的移工工傷死亡現場,對社會提出結構性的反思與探問。如呢喃般緩速的鏡頭,就像死後依舊無法自由的阮國非,在台灣成為孤魂,徘徊人行道、遊走雜草蔓生的荒地;探視在建築工地躲警察、奔跑摔成殘廢的移工,參與工傷死亡移工的追思會,最終回到越南老家,看孩子們打電玩,田野牛隻成群。
「這部分滿困難,我怎麼建構一個死去的人?我對他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我的理解會不會超過?都要很小心。」蔡崇隆知道,阮國非跟多數失聯移工一樣,為了賺錢回家而做各種工作,「但他為什麼偷車?為什麼吸毒?片子剛開始(拍)的時候,我也想知道怎麼回事。如果這東西我能夠解出來,這事件給社會的觀感會不會不一樣?但後來就看到密錄器,開槍跟後面(的處理)都已經是很大的問題,比前面的起因來得更重要了。」
低潮時遇真愛 漸入佳境
拍攝期間,蔡崇隆與團隊前往越南,當時家人為阮國非設置了暫時的靈堂,靈堂拆掉那天,阮國非的媽媽在蔡崇隆面前崩潰,哭得撕心裂肺。與蔡崇隆相熟多年、《九槍》製片李佩禪說,「那是我們拍攝中間,不確定現在所做的事情能不能對這一切有幫助,那時候他(蔡導)很無力,也對媽媽失去兒子的狀態感到很虧欠,但當下沒有說什麼。直到金馬獎時要他回憶拍片記事,他拖很久才告訴我,回憶這些讓他很痛苦。」

「他把這股無力感當作要把影片做好的重量,拍紀錄片對他很重要,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說 ,就會很用力地說。創作紀錄片像他血液其中一個支流,會不斷發生,碰到阮金紅之後,更激盪出不一樣的狀態。」李佩禪觀察道。
2008年,蔡崇隆在一場講座上認識阮金紅。嫁給蔡崇隆前,阮金紅曾有一段婚姻,前夫好賭、有暴力傾向,生活是無盡的苦難,她靠著自己蒐證,將前夫告上法院,結束那段關係,帶著女兒獨立。當時蔡崇隆正經歷喪母之痛,在彰化也沒有交通工具,阮金紅知道這個狀況,便把自己的摩托車借給他,每天走半小時去工廠上班,此舉也將他們的生命聯繫在一起,「她自己狀況不太好,還要幫助別人,」蔡崇隆露出有些無奈但溫柔的笑容,「我在人生的冬天後面碰到她,跟她在一起,一切好像就比較好了。」
他收養了阮金紅與前夫的女兒,三人一起搬到嘉義,由於阮金紅對影像感興趣,他教她拍攝剪接,2人漸漸成為工作夥伴,也發展出與過去不一樣的拍攝者與被攝者的關係,「跟金紅在一起,才有《失婚記》跟《再見可愛陌生人》,那是我們移民到嘉義生活的事,內容跟過去拍新移民紀錄片不一樣,跟金紅工作,她會用母語跟同胞溝通,有些東西更直接、更真誠。」
身處二種空間 獲得平衡
第二次採訪,我與蔡崇隆約在越在嘉文化棧,平房鄰近嘉義民雄交流道,在鄉間小路上有些顯眼,從院子到室內,布置著許多來自越南、色彩繽紛的掛飾、人偶與照片。抵達時,阮金紅正在院子的流理台清洗雞肉,穿著暖黃色的居家服忙進忙出。週末夜晚這裡通常熱鬧,幾個小時後,將聚集來自中南部各地的移工、新移民姐妹及新二代。

他們自己的家則位於越在嘉文化棧走路不到5分鐘處,蔡崇隆下班後通常二邊跑,「我目前有二種空間,一種是比較共產主義的,跟他們在一起;一種是像二水那種(有點獨居的),金紅比較習慣人際互動,到了一個程度我就滿了,就會回到我的空間,做跟學校有關的事、看電影,好像比較平衡,雖然我現在有家庭了,但不像以前家庭和工作要選一個。」
對蔡崇隆來說,他現在的身分不僅是紀錄片導演、大學教授,也是越南女婿,移民工社群的一分子。在此處,有年輕移工稱他和阮金紅「爸爸、媽媽」,像真正的一家人,彼此協助解決煩惱,蔡崇隆偶爾也會拿起攝影機拍攝他們遇到的事件;藉由申請計畫經費,他們也提供移民工法律服務、心理諮詢,「其實也有點在做NGO了,像一個海外之家、假日之家。」
拍片痛苦旅程 盼獲共鳴
「阮國非的海報現在都在我家三樓的神明廳,每次拜拜的時候都會跟他說,希望你可以讓你的片子順利,讓更多人知道你們的故事。基本上我想為他做的事就是—他在現實中像螻蟻一樣死亡,但在我的片子裡面他能夠像人一樣地活過來,享有跟我們一樣的人的尊嚴。雖然他已經死了,但是我希望他的死是有價值的。」
《九槍》這部紀錄片的痛苦旅程,對蔡崇隆來說也還未結束。年初《九槍》將會上院線,但不會走傳統映演路線,而是公益放映,之後每場放映,他還是希望到場跟觀眾對話,「如果票房很高,我一點都不覺得開心,還是覺得:有沒有消費他的生命?但是,如果你(觀眾)不太容易忘記這一部片,在心裡留下些什麼,知道有些東西不是編的、不是虛構的,是真的有人在那邊受苦,我把片子做好就夠了,(之後)要行動就是你們的事了。 」

這天晚餐,是由一個曾經在越南當過大廚的廠工負責,香茅雞湯香氣逼人。席間十幾個人,包含《九槍》中為阮國非自白配音的廠工阿尊、為《九槍》唱片尾曲的新二代學靜,還有住在隔壁的看護工、看護工的台灣男友、蔡崇隆的紀錄片友人…大夥兒自在坐在房間地板上吃飯,夾雜國語、台語和越南文,沒人能百分之百聽懂所有對話,但在這個空間裡,族群和語言已經不是什麼問題了。
★《鏡週刊》關心您:未滿18歲禁止飲酒,飲酒過量害人害己,酒後不開車,安全有保障。
★《鏡週刊》關心您:珍惜生命拒絕毒品,健康無價不容毒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