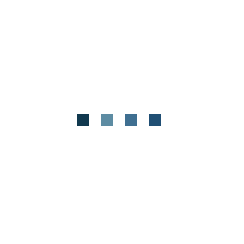太陽花的花語是希望
在太陽花學運的維基百科上有這麼一段敘述:「3月18日晚間,由於永和花店老闆林哲偉(編按:應為林哲瑋)贈送向日葵到立法院議場,隨後占領人士便不經意地把向日葵插在議場的講台上…透過眾多傳播媒體流傳後,造成群眾送來更多的向日葵…傳播媒體因此逐漸以『太陽花學運』稱呼這次占領行動。」
送花支持 意外成象徵
雖然名字被打錯了,10年前的新聞仍留下林哲瑋29歲時受訪的身影。畫面裡,他像失眠多日,帶著略顯濃重的黑眼圈,一臉疲憊,說話聲音也有點氣虛。我們後來才知道,他那時經營花店剛滿4年,兒子約2歲,成家、立業之餘還要支援學運,怎能不累?
10年過去,他不一樣了,臉變得削瘦,徹底脫去稚氣,也精神了。時移事往,很多事都不是當年期望的模樣,只有林哲瑋仍開著花店,十年如一日。他回憶那天,在臉書上看到有人要去立法院抗議,想著自己能做什麼表達支持?身為花店經營者,送花最簡單,因為剛創業不久,也沒什麼錢,就訂了2箱便宜又符合精神象徵的太陽花,請爸爸開車幫忙送過去。
他在晚上7點左右趕到現場,人比想像中多,「我走不進去,因為太多人了…我就一直喊:『有物資要進去!』但根本動彈不得。我連箱子都沒有開,就請他們傳進去,結果他們直接把花送到(立法院)裡面去…」問他得知學運以他送的花命名時的感想,他笑出來:「我嚇死了!」

林哲瑋不是那種浸泡在政治中長大的人,但台灣本就是政治島國,相關話題從未遠離他們家飯桌。林爸是深綠計程車司機,林媽是深藍公務員,林哲瑋還記得,家裡每逢選舉必吵,「爸爸很激動,好像有訴求必須被滿足、被聽到,所以總是很大聲…一講到國民黨怎樣怎樣,就開始爆;可是我媽就是覺得,一切安定、保守,不要有什麼爭執,在人家粉飾好的太平裡過生活就好了。他們追求的東西不大一樣,那我也會想,到底我要偏哪一邊呢?」
梨價大跌 敲反思警鐘
真正的啟蒙,來自外婆家在梨山上種的水梨,幼時他看長輩農忙,知曉農民辛苦:「每一個果子,即便只有一個小小的洞,已經不能賣了,但也不會丟掉,就削掉(損傷處)自己吃。你知道那些農產品都是花了很大力氣去照顧和維護。」
2010年,兩岸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降低或減免雙方貨物流通關稅,農業部官網仍留著當年的新聞稿:「日後台灣水果將以安全、優質、免關稅之優勢,提升國產水果競爭力,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2011年全台梨價大跌,農民血本無歸,外婆家的梨園開始在閒置地轉型種茶葉。林哲瑋心中出現疑問:「怎麼會變成這樣?怎麼你們支持的政黨做出的決定,其實對你們的生計,是比較不利的?」疑問累積到服貿時終於爆發,這次他加入了飯桌戰局:「人民可以違逆政府的決定嗎?他們的觀念是不行。我就覺得,投票不就是為了要政府通過對我們真正有幫助的方案嗎?後來變成這樣,你反而指責學生不對?」
此次受訪,他坦言曾和父母討論,他們的想法是:「確定嗎?我們做生意的,往來對象很多是深藍的…」我們一度以為學運花店會為生意帶來正面宣傳,殊不知當年狀況完全相反,「被cancel(取消)掉滿多家(生意)。」有問為什麼?「不可能問,因為那個時間點太集中了。就是事情發生、新聞出來沒多久,就有人突然說,上次跟你談的那個事情,後來我們公司有其他想法,所以先暫停。一個,你可能會覺得他們真的有其他考量,2個3個4個5個,不大對吧?」
當年賣太陽花給他的廠商,也曾明言表示要支持學生,僅收成本價,但當林哲瑋說想寫一篇文章表達感謝時,收到的回覆卻是:「不要。他們堅決地說,不可以寫他們的名字。」

一場轟轟烈烈的學運,最終帶來的只是生意上的損失。他至今不確定自己擋下了什麼?阻止了什麼?只有一路挫敗。5年多前婚姻平權公投是第一次失落,「那時公投我還幫我媽做小抄,教她按照順序投,結果後來投出來,真的是…原來我們以為的同溫層比我們想的薄很多。」
差不多也是那時候,外婆家的梨園在經歷幾次小範圍試種後,第一次迎來大規模改作,砍了一批樹。他大受打擊,好像關於童年的什麼再也回不來了。「梨樹枝在花藝工作裡,是非常重要的資產,所以我們想盡可能留下。我在新店的倉庫裡,就裝了一個小山的梨樹枝,都是我們在山上砍下來的。那是我外公以前去日本找來的品種,接枝養了幾十年,才長成那個樣子,直接化為烏有,真的是捨不得…」
堅守信念 十年如一日
外公外婆身為果農的勤懇,一直影響著他對待花草水木的心思,他知道每一朵花都得來不易,「怎麼可能讓它就開2小時,立刻進垃圾袋?」他開始和婚宴的新人洽談,是不是能在宴會結束後把花收集起來,捐給孤兒院和老人院?或把花放在店門口讓民眾自由拿取,「願意的話就捐錢(買花),我們每2個月把捐款湊成整數,再捐出去。」他這樣做,已經10年了。

就像10年前的太陽花精神一樣。林哲瑋說:「如果說太陽花(學運)帶給我什麼啟示,我覺得就是,不管力量有多微小,也可能會醞釀成一個大的力量。就像我無心插柳送的花,變成學運的名字。」
今年總統大選前2天,他在社群發文:「前幾天回家吃飯時,我媽突然緊張兮兮地把我拎到一旁,問我總統要投誰;說我爸看新聞說現在很多年輕人看抖音、支持親中政客,所以很怕我會投錯人(父親不敢直接來問我,才派我媽來探口風)。我回說:『他(林父)是不是忘記當年有幫我開貨車載向日葵到立法院前面發,才有後來太陽花的事情啊?現在花很貴,我可沒打算再來一次太陽花運動喔!』」
但他最後仍開車載著一束太陽花,隨我們重返青島東路拍照。拍攝結束後,將一束10枝的太陽花轉送給我,花遞過來,好像遞來一把火。我問,太陽花的花語是什麼?他說:「其中一個是希望。」
十年後才能說的羞恥
「左轉有書」書店牆壁上,用粉筆畫了太陽花學運時學生占領議場的場景,下方寫了一個提問:「十年前的今天,你在做什麼?」34歲的朱剛勇(本名朱冠蓁)回憶,那天她朋友衝進議場,手機沒電了,她送行動電源過去,之後每天晚上下班後就到物資站當志工,「就只是個路人。」

人生百味 扶持無家者
朱剛勇是「人生百味」共同發起人、《貧窮人的台北》策展人。太陽花學運那年成立的人生百味,至今10年了,該組織提供無家者相關資源,例如台北車站附近的據點「重修舊好」,讓無家者得以短暫休息、用餐、洗澡;專案計畫「人生萬事屋」 則組織無家者為清潔工作隊,到獨居長者、障礙者或弱勢家庭的家中幫忙清理打掃。除此之外,無家者沒有正式工作,往往沒年終、沒尾牙,人生百味也每年舉辦街頭尾牙,慰勞無家者一年來的辛苦。
人生百味成立的緣由,來自於學運時許多食物進入物資站卻放到過期,朱剛勇感到可惜,曾將一箱發不完的包子送到龍山寺給街友。「那時我連哪裡有街友都不知道,上網搜尋跳出台北車站、龍山寺,才知道那裡有這麼多街友。」她也從那時開始關心無家者、貧窮相關議題。

小學時她都跟男同學混在一起,因此被取了「剛勇」這個綽號。由於不滿臉書實名制,常使用這個名字,時間久了,也就被人稱為「阿勇」。她是高雄人,大學讀高師大設計系,喜歡閱讀社會議題書籍,畢業後到台北做韓國娛樂的行銷設計工作,卻沒有太大興趣;因為關注公平貿易議題,轉往非營利組織「公平貿易協會」任職,她關心社會議題,曾參加反核、洪仲丘遊行。
朱剛勇印象最深的是3月23日,學生攻占行政院那天。她回憶,當天吃晚飯時收到訊息,立刻衝到行政院前,那時警察已開始集結,周圍有人一邊喊衝,一邊看著她,但她無法動作,就愣在那裡。「原本想像自己會一路很順地衝進去…那個不敢再靠近的恐懼感很大。」
轉化內疚 擁抱無力感
她說,當時內心有強烈的拉扯。一方面覺得,自己經歷了各種思辨,這一刻來到現場,可以成為一個挺身對抗制度的人;但另一方面,她又想著種種不衝的理由,「我明天要上班、我在NGO工作、我在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等等,可是自己知道,那些理由都是為了不要過去。」
「我那時候人在那裡,但我走了。」書店裡,朱剛勇細細剖析,她說當時心裡「有一種很巨大的、複雜的無力感」,也有自責跟內疚的心情。「而且還伴隨著一種…」她想了一下,神情有點難過,「一種羞恥嗎?後來看到有些朋友提到那天被打、被拖走,我其實那天在現場,但沒有進去。我覺得心靈的那股羞恥感,一直到10年之後,到現在才有辦法說出來。」

她說太陽花學運對她最大的影響,並非只是拿一箱發不出去的包子給街友,進而成立非營利組織,而是看到那個不勇敢的自己。「所以我後來更能夠去體諒人無法做某些事情。那個心靈狀態,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次體驗。」她學會體貼,體貼他人的無力,也體貼自己的無力。這也讓她能更能貼近無家者、貧窮者的處境。「那個不勇敢、不光榮的,甚至是被貼上汙名的狀態,讓人特別想要、特別希望被社會所理解跟講述。」
她至今不曾和衝進行政院的朋友們講起這段過去,一方面還在思考該怎麼說,另一方面也缺乏開口的契機。朱剛勇說,那天離開時,身邊另一個也不敢衝的朋友對她說:「沒關係,我們回去再想想看還能做什麼事。」回家後,她一邊看警察鎮壓的影片,一邊爆哭。
「再想想看還能做什麼事。這句話對後來的我,一直是很重要的提醒。」她笑說那陣子,工作特別奮力,奮力到老闆都疑惑,不知她為何有這樣的轉變。「好像很拚命地想要證明自己,那天沒有去,確實還有其他事情在做吧。」
落地做事才踏實?
採訪這天,31歲的李嶽,早上先到新竹峨眉教老人家彈樂器唱歌,下午回苗栗南庄開幸福巴士,載一位獨居的客家老奶奶回山上的家。偏鄉客運因營運不佳,行經路線縮減,許多地方交通需要替代方案。公路總局的幸福巴士政策,讓偏鄉部落的長者,可以透過預約的方式搭乘,外出看醫生、買生活用品後要回家,不致於無車可搭。

投入社運 抗爭衝前線
李嶽是國科會偏鄉交通平權調查小組專員。他每天早上6點開始接電話,幫地方居民預約,有司機請假還需幫忙開車。目前他正在對峨眉鄉進行調查,規劃幸福巴士的行經路線,但要經營並不容易,得找車、找營運的啟動資金。車需要人捐,而啟動資金需要100多萬元。
李嶽曾經翻過立法院的圍牆2次。第一次是在太陽花前一年的7月,立法院開服貿公聽會,反服貿團體在大門口抗議,呼口號講訴求,就衝了。當時他閃過警察,迅速翻過圍牆一躍而下,「結果沒有人跟上,也沒有警察要理我。」遇到這種情況,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默默從側門離開。回到正門,「又翻一次,哈哈哈哈!」第二次,一翻過圍牆他就往立法院裡頭衝,「哇,一坨耶,大概有10個警察,我往他們身上衝,當然就被押起來了,警察說:『好了啦,不要進來啦,來這邊沒有用啦!』」
隔年,太陽花學運發生。當晚反服貿團體先在立法院旁抗議,後來翻圍牆占領了立法院。但李嶽那天不在,「我那天落跑,沒去,那時也沒人想過真的能衝進去。」當晚他收到消息,馬上搭晚間11點的末班客運從新竹前往台北支援,跟眾人一起進行組織分工,他當場控,試著把人群留在立法院周圍,讓警察無法清場,緊繃狀態下連續3天沒睡。

太陽花學運那年他大三,就讀清大人文社會學院。他高中在圖書館讀了馬克思與共產黨宣言,深感震撼,因此決定大學要主修社會學。他是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成員,大一開始參加抗爭,苗栗大埔案、華光社區、反媒體壟斷、反漲學費、士林王家、國台辦來台,無役不與。
當社運學生,特別激烈的,就屬擋拆遷的場子。「真的是最硬的,大家想辦法拖延警察排除的速度,在室內用鐵鍊把自己跟樓梯綁起來,或是在很狹小的地方躺下,警察很難抬啊,火氣很大,記者又拍不到,就對你動手動腳。」有次他惹惱搬他的警察,「直接膝蓋下來頂我的肚子。」他形容那過程往往是腎上腺素分泌旺盛的狀態,提起有一次抗爭過後,早上10點他一個人走在街上:「陽光普照,大家過自己的生活、走路、做生意,很奇幻的感覺,你明明經歷生死交關的事情,但是你走出來,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對於太陽花學運待在議場的那段日子,李嶽說印象深刻的回憶不多,他翻臉書找當時發的文章,一些事情說得瑣碎。深刻的,反而是屬於社運學生才有的感觸。「那幾年跑社運都有很孤單的感覺,覺得自己很邊緣、很少數,大家會說你很棒、加油,可是他們一樣過他們的。到太陽花學運的時候才第一次看到,原來社會運動有這麼多人支持,這麼多人想參與這些議題,那是我第一次有這樣的經驗。」
學運組織 宛如打選戰
自學運開始時就待在議場,以為他會講得熱血激昂,但沒有,李嶽憨厚的笑容中帶點寂寥。3月30日大遊行之後,他覺得無事可做,便離開台北回到學校,投入其他事務。雖然他很靠近決策圈,每天參與會議,但對他來說,太陽花學運並非他所熟悉的社會運動,感覺身處其中的自己,成了社會學所形容的、制度中的一顆小螺絲釘。「組織很大、分工很明確,它更像在打一場選戰,我後來做政治工作後才意識到,那(太陽花學運)其實是一個競選總部,甚至是比競選總部更大的組織規模和運作方式。」

李嶽說,那種無事可做的感覺,對他影響很大。「做社會運動、做議題,落地這件事情很重要。」大學期間成天跑社運場子,時間久了,他對光是嘴巴講理論感到厭倦,於是畢業當兵,退伍以後,他先當了四年的新竹市議員助理,後來想做些過渡期的工作,女友到新竹峨眉鄉做地方創生,他便跟著去,在鄰近的苗栗縣南庄鄉做交通平權的專案人員,就這麼待到現在。
他說所謂的落地,就是人在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耕耘。「以前搞運動,到處參加議題講座,到處跑,幫人家寫新聞稿什麼的,可是很空虛。我聽了很多很重要的議題,我知道什麼東西是正確的,什麼東西是該關心的,可是沒有做事。我現在做的工作,接觸到真的人,雖然事情很小,可是很扎實。」
台灣學生保護了我們
「到現場有什麼用?可能沒屁用。」「想衝,卻總問自己憑什麼?我又不是台灣人。」2014年3月19日清晨,港生Candy滿心糾結,跳上新竹客運首班車,從清大直奔立法院。
32歲的Candy與我們重返318運動現場,她滑開臉書,翻找10年前的貼文,有青島東路現場照,也有服貿爭議懶人包。她蹙起眉,「我當年寫臉書,怎麼這麼中二?」此刻她身旁坐著35歲的香港友人Franki,2人在台灣熟識,一聊才發現當年都在學運現場,且都加入後勤工作小組,頻繁進出的工作地點,就是徐州路上的台大社科院舊校區。

無痕參與 烙愧疚傷疤
Candy在香港讀完高中,隻身來台就讀清大人文社會學院。儘管香港當時蘊積不少社運量能,但Candy對故鄉社運並不熟悉。台灣爆發318,是她首度參與大型社運。
「同學告訴我:『妳是香港人,別去現場。』到了324,要衝行政院時,很多人說:『妳是香港人,不要進去行政院。』」當時22歲的Candy陷入拉扯,「大家阻止我,但我不想什麼都不做。我需要拿捏:怎樣的風險,是我可以承受的?」
Candy在街頭蹲3天,回清大洗一次澡,又回立法院。她發現,比起站在台前拿麥克風,自己更擅長行政後勤;學長帶她進台大社科院階梯教室,與各校十多名學生協作,「我一直做圖發文,幾點幾分,請大家在哪裡集合,類似『動員文』。」
現場數台電視輪播,每人埋頭筆電,階梯教室沒有窗戶,她不知破曉日落,只知累了躺下,醒了工作。該小組很謹慎,人員進出須配戴識別證、核對名冊,唯獨她例外,「他們說我是香港人,不能留刑事紀錄。所以,所有工作名冊、識別證,都沒我名字。」
「我是318運動隱形的參與者。我很愧疚。我是小編,後來發文動員大家衝行政院,大家被打了,我卻在階梯教室,後續也無法和任何行動者討論。」占領行政院行動在鎮壓、清場下落幕,「社科院派」立刻解散,Candy帶著難以名狀的罪疚,無人訴說。她曾耳聞有心理諮商團體願與學生聊聊,尷尬的是,她的名字不存在任何名單,成了被遺落的人。

「我一直覺得自己很邊緣、沒有被看見。可是有時候,只是很想做一些事、說一些話,讓自己也貢獻什麼。想衝的心情,比拉住自己的動力還要強。」太陽花落幕不久,香港爆發雨傘運動,許多Candy熟識的港生,機票一買衝回香港;她沒衝,留在台灣。
「即使我飛回香港睡街頭,也就是空拍機下萬人裡一個黑點。我一直想:我個人如何發揮最大效果?」有了318經驗,她學會盤點自身能力,寫信給教授,向老師們「借課10分鐘」。此後2週,她帶著自己做的PPT穿梭教室間:「大家好,我是香港學生,請借我10分鐘,讓我講一下香港發生什麼事。」每遇哽咽,話語停頓幾秒,台下學生總會等她,聽她說完。
這是Candy首次「國際倡議」經驗。後來,她看到清大學生發文,表示因她分享,更理解港人立場,「我覺得…我好像有做對選擇?我一直覺得自己很渺小,但嘗試讓自己功能最大化。」
「318留給我很多困惑。我加入一個團隊,在緊急凌亂之下被解散,我又忽然被剝離了。當時(社科院派)到底為什麼解散?我有沒有貢獻過一點什麼?」但困惑未必全是壞的,「如果有什麼影響到我,可能是之後參加社運時,若我有量能,會去關注更邊緣的人。」
比起Candy的運動傷害,Franki的318記憶不那麼痛苦—彼時他就讀台北藝術大學研究所,此前,他參加過樂生反迫遷,和警方有對峙經驗。學運期間,他進出社科院,協調物資場地,占領行政院行動中,他加入「衝組」,翻過行政院圍牆。
「參與樂生的時候,台灣人也保護我。警察登記姓名,學生就拖住警察,叫我快走。」許多年後Franki發現,這種保護並非「叫你不要參加社運」,而是「幫你降低傷害」。占領行政院現場,他聽著何韻詩〈光明會〉爬過圍牆,然後警察來了,眾人要他快倒下,趁亂以救護車掩護他出去,「台灣學生都知道,只要我被抓,政府有權遣返我。」
關注人權 在台撐香港
學運隔年,Franki返回香港,試過前往其他國家工作。他最大的創傷發生於2019年,香港反送中;其後他輾轉各地,2022年起落腳台灣,任職NGO。2023年,他以香港監獄書信往來為題,創作劇本〈寄:〉,獲台北文學獎。
他們的離合聚散,都在台灣。Candy目前亦在台灣任職NGO,關注香港人權,她有時會想起318期間,某天清晨,青島東路人們睡成一片,樹上布條印著「媽媽請不要擔心、我很安全」,她見警察在發呆,趕緊拍照,傳給在香港的媽媽,假裝一切平安。

「身為香港人,有很多不得不考慮的風險,需要隱身、妥協、不能用本名和大家說話,呈現出來的,往往不是自己最理想的公共參與樣貌。為什麼很多人匿名,還要受訪?就是希望有些故事被知道、不要落掉那些在陰影裡的人。」心中軟肋是家人,談到雙親,她眼角潮濕,「我爸媽一直不知道,318運動裡,我待過一個社科院裡的小組。」
「我在318做的事,和現在工作很像…爸媽還是不曉得,這些年我在台灣做什麼?」春日的社科院忽然颳風,吹亂她包上布條,「我一直帶著這個,」她攤開皺舊布面,印著「台灣守衛、撐出香港」—這條皺布,她也許更想攤開給父母看。
去平行時空看太陽花
同一場景,可能有無數視角與記憶版本。318記憶以不同形式存在;中國女生小羽(化名,26歲)10年前透過網路「誤闖」立院議場,10年後的她首度來到台灣,仍記得那個「不在場的現場」。

祕播影片 埋自由種子
2014年3月,16歲的小羽就讀中國某省會的重點高中。一日午休,歷史老師要全班拉上窗簾、把燈全關了,播放318學運影片。她至今想不透:老師如何得到那些影像?「印象很深,視頻(影片)裡學生們非常激動,占領立法院。從那畫面看來…所有人都上街了。」「老師說:『你們自己看看台灣年輕人都在幹嘛?然後你們在幹嘛?』」
「我們要考高考(聯考)呀!」小羽向同學抱怨:「我們也想上街,但有這種條件嗎?老師不該把這說成是我們的錯,好像我們兩耳不聞窗外事、不夠清醒、不夠嚮往自由。」「我們每天被困在教室裡,手機都不能碰、不能翻牆出去看新聞。然後,你反而怪罪學生,說我們像傻子?」
午休結束,小羽回到升學正軌。「我當時很討厭這老師,覺得他廢話很多。」印象裡,老師上課常陰陽怪氣影射時政,還戲稱毛澤東是「太祖」。當時習近平剛上台,尚未獨攬大權,她高中班會主題是「習大大萌萌噠(很可愛)」,「大家對習近平印象特別好,覺得他帶來希望…」對照今昔,她失聲大笑:「現在想起來,好想吐。」
談起高中同溫層,小羽有些尷尬,「當時大家都從現實角度去理解社會運動,沒有真正思考:這意味什麼?台灣和香港年輕人,為何上街?」同年,香港傘運爆發,「我們不從政治角度去理解。有同學打算去香港玩,他們最在意的是…出去玩,會不會有危險?」
我們向她確認,老師曾說明太陽花運動脈絡嗎?她搖頭,「理解這些事,都很碎片化。大家把『反服貿』單純理解為『反共產黨』,有些人會理解成『國外在鬧事』。」為了核對記憶,小羽詢問高中同學小傅(化名,25歲)。我們聯繫留學歐洲的小傅,他確實記得這場「放映」,畢業後,他亦得知歷史老師曾因課堂言論,被家長舉報。
與太陽花學運本身無關,高中畢業前,小羽和學長閒聊,學長試探:「妳知不知道天安門『那個事』?」小羽懵然。學長說:「妳不知道?死了好多人啊。」
「當年,我沒有正常渠道去知道歷史。」她不知六四、不知學生為何抗議、不知坦克會輾過人。她考入明星大學,獲機會出國,接觸「牆外」媒體。201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過世,她卻不知劉曉波是誰。「我上網查,愈查愈多,發現原來我這麼無知。我大哭一場,哭得特別難受。」
劉曉波的死,燃起小羽對所處世界的好奇。她惡補台港近代史,某些時刻,會想起那位討厭的歷史老師—畢業後,她也耳聞老師被舉報、調職,也許,不只一人舉報他,「我開始理解,老師當年為什麼把教室弄暗?為什麼要偷播太陽花視頻?那些陰陽怪氣、那些調侃,可能來自他的壓抑。他可能想透過太陽花運動,啟發我們一些東西…可是當時,他無法實現。」
歷史老師的下落,再無人知曉。但小羽清楚知道一件事:「那個午休,老師把窗簾拉緊,卻從此替我打開一扇窗口。」

走出牆外 援白紙運動
那扇窗通往世界。2024年,小羽初次踏上台灣,觀摩總統大選。她做足了功課、報名講座,去現場看開票。當監票人員開始唱票,她很激動,「這是公開實踐民主,而且這是用中文說的!海峽對面的中文世界,對我來說,就像平行時空。」
小羽大學畢業後,曾前往北京一所非營利組織實習,只是該組織最後被迫關門。2022年底中國爆發白紙運動,她在日本加入聲援行列,負責社群營運、策劃沙龍。當中國留學生們站上東京街頭聲援白紙運動,她蒙面舉牌,站在人群中。
這是她首度參與社運,面對內部矛盾場景,卻頗有既視感,「我看到社運的複雜性。太陽花學運、雨傘運動,內部都有矛盾;白紙運動後,我也看到類似的矛盾。」「遊行,會給人一股熱血感,大家常被簡單情緒支撐—反共產黨。但人們其實沒仔細思考:我們該為社會做些什麼?」
「10年前,一個中國的老師,很祕密地帶學生看這麼敏感的太陽花影片,現在想起來,很不可思議。10年後的今天,我才意識到這很重要。」她無法找到歷史老師,但開始思索更重要的事—例如透過民間串聯,不同國家的青年可建立共同問題意識和目標,「性別議題對我啟發最大,而且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新潮流,也是目前大家共同可以發聲的議題。也許,我們敵我意識不必那麼強?我們可以多看到彼此的連結點,可能是反抗傳統父權制對女性的壓迫、或反抗資本主義對勞動者的壓迫。現在,我更在意這些。」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
李宗霖還記得行政院清場那天,警察變成機器的眼神。消息出來時他正在吃飯,決定趕去支援,搭計程車,「司機還不算我們錢,叫我們要加油。」晚上7點多,開始有人和警方起衝突,他出面阻止,努力維持「非暴力抗爭」的秩序,「然後警察就開始清場。他們變成機器。」

決心改變 參選市議員
變成機器,是什麼狀況?是真的從他們眼神或裝備,看出他們變成機器,而不是一個人在面對另一個人了?李宗霖說:「完全是啊。他在意的是效率,有沒有辦法準時把你們清完。所以他們就是把你拖啊、在地上揍啊打啊,對你飆國罵啊,把你清走。」
凌晨1點,撐不住了,「我那時穿了3件衣服,都破了,所以你知道那個力道其實是滿大的。」他退回立法院附近的醫護站做處置,到醫院驗傷,早上6點多才回過神來:「靠么!這個國家怎麼會變這樣?」
外傷容易處理,內傷麻煩。李宗霖坦言清楚自己在學運中的位置,就是一個人頭,哪怕時代造浪,也自知只是小小的浪花。不過面對「國家怎麼會這樣」的疑問,他終究無法不去想,說:「從小念書,在體制內長大,我(那時才)開始思考我到底要做什麼?我一路看書,聽人講,找答案。」

花了半年時間消化,得出的解答是參政。2018年,他決定參選台南市議員,走上更艱難的革命之路。父母都是魚販,苦幹養活一家子,對孩子的期望無非是好好念書、工作。有天,爸爸忽然找他吃飯,出言相勸:「不要涉入政治,你沒有要出去留學也沒關係,就好好考個建築師…」
為了說服父母,李宗霖做了PPT簡報,解釋自己為什麼要參選。如今他已找不到簡報檔,但依稀記得最明確的思路是,太陽花運動不就是年輕人想要出來改變點什麼嗎?「當然改變也可以從其他地方開始,可是政治明明是我們國家最大的動能,卻也是最大的黑洞。很多政治人物很糟糕,你不想被這些人統治,就自己出來選,對吧?」
也許是簡報真打動了父母,李宗霖最後借到20萬元作為競選經費,加上政黨支持,總共花了150萬元。他笑出來:「大家聽到的回饋都是『你怎麼這麼便宜!』你知道有些國民黨的人,(參選)都是1千(萬元)在撒的。」
台版長征 見民主遺痕
那年他30歲,無政治背景,卻能選到只差500票就當選。他不諱言「太陽花」是個Bonus,甚至超脫了政黨色彩,可以得到大多數年輕人支持。那也是一群「沒有錢」的人,而他和那些人太像了,畢業後服役、工作,走進22K政策發展出來的絕望職場,漸漸活成同世代共苦的鬱悶模樣,「當時(流行的)書籍就是崩世代啊、反貧困啊…」
走上街頭的也多是這些人。李宗霖回想從電腦裡看到有人衝進議場抗爭的那天,他人在成大圖書館,為出國留學做準備。那時他26歲,在建築業界領低薪當營繕專員,工作內容包山包海。那是教授介紹的工作,但得知低薪狀況,教授自己都覺得抱歉。出國留學看似是突圍的唯一路徑。
直到另一條路出現。3月19日,他搭第一班高鐵從台南到台北,再轉進青島東路。那時他沒有想到,此行一待就是一個月,接著影響了未來10年的人生規劃。

2015年,他加入基進黨成為志工;2016年為了輔選,開啟一趟效法切.格瓦拉的旅行。切.格瓦拉當年在長征中一路向北,親見了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李宗霖則是從美麗島出發,一路經過台南湯德章紀念公園、嘉義二二八紀念碑、苗栗大埔的張藥房,最後到台北的鄭南榕紀念館,那是他自己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
2022年他再次參選,順利當選台南市第十選區議員。採訪這天,他騎著老舊的摩托車現身,車上還貼著校園停車證貼紙和台獨貼紙,都斑駁了。他帶領我們穿過成大校園,人好多,「因為今天有稀有的寶可夢,還有同志遊行。」年輕的人們和我們擦肩而過,我問他,怎麼看待現在的年輕人?李宗霖說:「我覺得我老了,我才36歲,已經沒辦法跟20幾歲的人聊天…」他談起過往到校園演講,自我介紹還可以用太陽花簡單定錨,10年過去,沒辦法了,「他們那時候都還只是小學生而已…」僅僅10年前的歷史,被翻頁了。
再回首10年前的那一晚,和他一起守在青島東路的朋友們,「都回去做建築了,只剩下我還在做政治工作。」那是距他已遠的平凡上班族生活,他也曾想過當年若沒有北上,若沒有被警察打傷,若沒有騎摩托車去旅行,若沒有看見那些在民主路上灑過熱血的前輩身影…人生沒有如果,李宗霖說:「是這些事情,促成了現在的我。」
一邊育兒一邊當公民
張淑惠拿著一疊泛黃的自製繪本,跟我們講解服貿:從前從前,各村落居民以物易物,後來出現貨幣,大家都換到自己想要的物質,生活變得更好了。可是,有一天,金礦國的商人帶著滿滿的金子,想跟村民交易。村民們有人贊成,有人反對,贊成者認為貨出去可以發大財,反對者認為金礦國一直想併吞我們,這背後一定有陰謀。繪本最後,各方吵了起來,怎樣的交易才是好交易?沒有明確結局,張淑惠補充:「它其實是在說協議要對等,每個人要思考,自己做決定。」

親子共學 街頭變教室
她帶我們來到濟南路群賢樓前,10年前,200多個家庭帶著小孩來此搭帳篷,埋鍋造飯,輪番守夜,她比劃著:「這裡有個烹飪區,這裡有個繪本遊戲區,小朋友就在馬路上踢足球,上廁所就去濟南教會。」她說,最多曾有約20頂帳篷,並排到濟南路中央,延伸近中山南路,帳篷上貼著對待小孩的原則:不打不罵,不威脅利誘恐嚇。她解釋:「很多人送糖果給小朋友,純送沒關係,但我們希望不要用糖果吸引小孩,大人都會這樣玩孩子嘛!不過這邊的人都對小孩非常友善。」

10年前,張淑惠是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理事長,她擔憂馬英九政府的傾中政策與不平等服貿協議,3月18日晚上,她看到學者靜坐抗議,9點與先生、7歲的兒子到場聲援。接著,先生跟著群眾翻牆進入立法院,她帶著兒子在馬路上留守一夜,「我跟先生本來是教育改革夥伴,有了孩子之後成立親子共學,我們很希望帶動有孩子的家庭繼續關心社會。」
她記得那晚:「我跟另一個家庭留在那邊,幸好我們經常露營,有幾張露營椅,小孩睡在野餐墊,因為很靠近水溝蓋,腳上都是蚊子叮。」怎麼跟小孩解釋現況?「有一件事情要被政府決定,可是沒有經過商量討論,這是不民主、不合理的,所以我們要表達抗議,要經過討論、取得共識。因為我們從小不打不罵,不管要帶他去哪裡,都要經過商量討論,小孩非常有感。」
兒子席地睡在野餐墊上的照片在臉書上被大量轉發,鼓動更多家庭帶著小孩來到現場。親子共學認為教育並不是在課堂上,而是在生活中,幾天之內,抗爭演變成在議場外保護學生的長期抗戰,口號是「學生不退,親子不退」,街頭民主教室順勢形成,學者短講、群眾對話、講故事…街頭成了大型自學進修社群。

「國家讓這麼年輕的孩子翻牆進議場,我們是更大的成年人,不好只交給他們去承擔,(當時)有這樣的心情。」整整20多天,她頂多偶爾回家洗澡休息,其餘時間全都在街上。「不知道警察什麼時候會來清場?那個恐懼一直在。一定要守住這裡,白天人很多,晚上人一少就感到緊張,尤其害怕警察使用暴力。」街頭上,小孩與警察盾牌形成鮮明對比,「小孩也會問,警察不是保護我們的嗎?」
做足功課 倡理性討論
恐懼的最高點是行政院衝突,她擔心接下來會暴力驅離濟南路,「一直在想怎麼保護小孩,但這時候,小孩反而是安定的力量,他就是吃、睡、遊戲,過他的日常。」我們與張淑惠如今17歲的兒子聊了聊,他記得在街頭玩得很開心,就像一場遊行或露營,長大後知道是太陽花,覺得「很酷,原來我在歷史現場,有出到一份力。」
尊重兒童需要學習。張淑惠舉例:「那時候街頭有香腸攤,只要排隊就可以免費拿到一根,有一度阿伯說:『小孩半根。』我們就跟他討論說小孩也是一個人,也要一根,阿伯猶豫一下就答應了。阿伯可以溝通,但當時馬英九政府沒辦法溝通啊!」
運動退場後,張淑惠持續關切核能、兒童遊戲權等議題,並希望培養與不同意見者深入對話的能力,邀請審議式民主倡議者呂家華來親子共學團分享,「家華介紹審議式民主的程序,帶大家實作、討論,還有事前的資料準備。這打破我的想像,不是一群人意見交流就叫作多元,還要提供相關資訊。還沒有做任何審議討論之前,大家會依照自己的經驗、直覺做決定,但當我們得到更多資訊,有時間充分思考,有憑有據討論之後,才能夠做一個相對理性、並且盡可能符合公共利益的決定。」

她和一群家長們開始土法煉民主,例如:大家想要更理想的公園遊戲環境、更活潑的公共空間,就讀資料和國外案例、相關法律,找法令制定者溝通,挑戰官僚系統。2019年,共學團創立政黨「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2018、2022年她2次參選市議員,社群內部討論各種議題,都會先閱讀相關資料再討論意見,她笑著總結:「一邊育兒一邊當公民。」
回想10年前露宿街頭那20多個夜晚,她每天都懷疑真能擋下服貿協議嗎?她記得撤離那天好開心,終於可以回家睡覺,「努力是值得的,我在那邊睡20多天,真的有守住。」